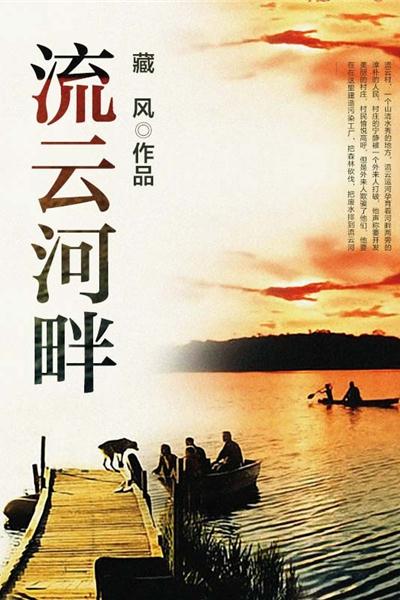民国初年,中国玉器市场出现了空前繁荣。1860年、1900年外国侵略军两次攻进北京,掠夺圆明园和清宫的玉器珍宝;1911年,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将宫中玉器携出皇宫。期间流入民间的玉器成了当时玉器市场的重要货源,也成了达官贵人、商贾和珠宝行追逐纷争的收藏品。与此同时,宫廷玉工回归民间,玉器结束了专为皇室所用的千年历史。
凌晨,月黑风高,一个瘦小男子捧着包袱疾走在苏州专诸巷,身后不远处有鬼影跟随。瘦小男子走到街角的“珍品斋”玉坊急切叩门。
少顷,屋内灯亮,传出问声:“谁?”
门外低声答道:“送货的。”
门开,瘦小男子仓皇闪入。
开门的是玉坊学徒单常青。
屋内昏暗的灯光下,来人用颤抖的手将包袱打开,一件洁白如雪的玉器骤然呈现。那是一尊由七朵梅花相托的玉杯。
“一捧雪!这不是传说明代宫中消失的玉杯吗?”单常青震惊。
来人愕然,“小师傅见过‘一捧雪’?”
单常青摇摇头。望着玉器,欣喜的神情突然凝固了,渐渐锁起了眉头。
看到单常青表情转阴,来人小心翼翼地问道:“有何不妥?”
“这是赝品。”单常青决绝地说。
来人追问,“小师傅何以断定这是赝品?”
单常青直言,师父说“一捧雪”出自宗师陆子冈之手,陆子冈非新疆和田玉不用,眼下此物却并非和田玉。来人喜出望外,如得救星,他低声说:“此物确为赝品。小的千里迢迢寻来,就是想求陆永冈师傅选用上好的和田玉,另仿制一件‘一捧雪’。”
单常青说:“那又是为何?何况,我师父从不仿冒宗师之作。”
来人说实不相瞒,自己的家族为了这明代世传的珍品前前后后死了十余人。眼下家族又将遭到灭顶之灾,能不能躲过去,全靠和田白玉的“一捧雪”赝品了。听说陆师傅家传有陆子冈的“昆吾刀”,若能速速出手相救,家族定能遵守祖宗留下的“人生玉存,人亡玉碎”的训诫……说罢跪拜不起。
原来他们家族所付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保“一捧雪”真品。单常青不再多问,扶起他说:“我只是个学徒,做不了师父的主,你不如明日再来见我师父。”
也只能如此,来人留下物品,说好天亮再来,便匆匆离去。
单常青怔怔地望着赝品,正待仔细琢磨,忽闻门外有异声,忙出去张望,却见刚离去的年轻人已倒在血泊中,气若游丝。单常青慌忙将其扶起。年轻人说:“小的名叫李莫明,家在鄂北大李营村,父亲临终嘱我来找陆师傅,‘一捧雪’现在……”话未完便含恨而去。
“不行,李莫明不能死。”岳明手里拿着作文本,看到这里不禁提出异议。弟弟岳川漫不经心地看他一眼,“为什么不能死?”
岳明说:“他死了,‘一捧雪’真品怎么到我师父手里?”
岳川看到哥哥入戏了,暗自得意。
“问题是‘一捧雪’真品在你师父手里吗?”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粉笔在地上草草几笔,一幅“独钓寒江雪”脱手而出。岳明欠身看了一眼,本想夸一句,但今天他不想让弟弟得意忘形。
“他说在,那就一定在。”
“你这是迷信师父。”
每天黄昏,弟兄俩都会坐在家门口,一个学徒工,一个高中生,沐浴着邗江江面上吹来的晚风,不识人间愁滋味,闲聊笑谈中。
岳明说:“告诉你,这篇东西不要给别人看了,要不想被我师父骂的话。”
“我写的是民国小说,你师父凭什么骂我?”岳川不屑地样子。岳明反驳,“你写小说就写小说,为什么要用他的真名?”岳川开心地说,“好玩啊!再说,天下又不是只有一个单常青,还有叫洪常青的呢,人家可是红色娘子军的党代表。你放心,你师父不会找你麻烦的,他的故事,婵儿讲给我的比你多。”
提到婵儿,岳明有些蔫了。婵儿是岳明的师妹。师父单常青经常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俩徒弟听,但也有可能单独给婵儿开小灶,因为师父更偏爱婵儿,说她有灵性,生来就是雕玉的料。
岳明忍不住问弟弟:“婵儿还讲了什么?”
“婵儿说单师傅是陆子冈的十八代传人,手里有陆子冈的昆吾刀,还有陆子冈留下的真品‘一捧雪’。其实跟你讲的一样,只是……”岳川说着突然喷笑了。
“只是什么?”
“只是我不信。”
岳明认真地对弟弟说:“你还别不信,我师父不说假话。”
“哥,你还真别信。”岳川也认真地说,“我们历史老师说,陆子冈是明末最著名的琢玉巨匠,是中国玉雕史上最负盛名的艺术大师。无论是书上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说他的存在是空前绝后,一身绝技却不授徒,他哪来的传人?至于那把昆吾刀,我早就对你说过……”
见哥哥瞪着眼睛,岳川打住了话头。
“好了,我不说了。”他说,“哥,我听妈讲,昨天厂里调你去供销科了,你不是立志要成为陆子冈那样的玉雕大师吗?理想就这样被改写掉了。你师傅连个‘不’字都没说吧,他不是很看重你的吗?”
“岳川,你怎么老和我师父过不去?”岳明生气地制止弟弟。岳川说,“谁让他故作神秘,说什么昆吾刀秘不示人,还把我从工房赶出来。”岳明急了,“你一个小毛孩子竟然跑去要看昆吾刀,那是厂长都不敢提的要求,你以为你是谁?再说,调供销科的事,我师父哪里拗得过厂长啊。”岳川说,“你师父要是有昆吾刀,厂长拗不过他才对呀。”
岳明说:“你小小年纪,尽琢磨些没用的。告诉你,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单常青永远都是我师父,不许你再编排他。”
这时,他们的母亲从家里出来,冲他俩喊道:“你们两个要不要吃饭啊?”
兄弟俩这才发现天色已晚,赶忙起身。
岳母四十多岁,仍然风韵十足。她用宠腻的目光望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俩孩子聪明有德性,这点随他们的父亲,而五官端庄、身材高挑,则像她这个母亲。等他们健壮起来,在湾头镇就是玉树临风的一双。
“岳川,你哥明天要去和田。今晚你要让他早睡,别再缠着他雕你的小玩艺。”母亲说。
岳川十分惊讶:“什么?去和田?这么重要的事怎么没人告诉我啊?哥,带我去好吗?”
母亲说:“高考前,你哪儿也别想去。”
岳明在弟弟羡慕的目光中,昂首挺胸走进家门。岳川在他身后大喊:“岳明,你要能登上昆仑山,你就是大英雄!”
半个月后,昆仑山就在岳明脚下了。
他高声大喊:岳明——
声音在众山中回荡,转瞬消失得干干净净,只留下大风飒然,飞雪翻卷。
岳明有意挺直了他刚刚发育成熟的身驱,仰起那张英气逼人的脸,为的是让昆仑山的诸神看清楚,他历尽艰辛达到的高度,是他这个年龄很多人的梦想。然而,他内心的自豪感有多强烈,身体痛苦和折磨就有多凶猛。但愿诸神不会发现,因为高山缺氧他正瞳孔放大,头痛得要爆炸。
岳川说神仙不会老,就算老得化入混沌,也还在昆仑山天梯能够到达的地方。岳川读书多,总能讲出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岳明则是弟弟的忠实听众和读者,他无数次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弟弟故事里的英雄。现在好了,能从扬州到达昆仑山顶的人,除了科长,就是他岳明了。就凭这一点,岳川是不是可以把哥哥的故事写到他的小说里呢?
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岳明二十岁。二十岁是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是在未来的许多年里会反复回忆起的美好时光。
岳明因为从小长得白净单薄,母亲没舍得让他加入上山下乡的洪流,十六岁中学毕业,他进了湾头镇的玉器厂当学徒工。父亲说,“天下玉,扬州工,源湾头。你出生在湾头镇,为何不近水楼台先得月?学了玉雕手艺,这辈子衣食无忧。”
扬州的玉雕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期,藏玉盛行,扬州和苏州一样成了朝庭的御用大作坊,进入宫廷作坊的玉工也多为苏扬人。后来朝廷没了,玉石集散地却在扬州沿袭下来,老艺人蛰伏,高手云集,如同白玉、青玉、墨玉、碧玉,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江湖。
三四年的光阴很快就过去了,整天和玉石打交道,岳明渐渐强壮起来,他爱上了玉雕,尤其是跟着单常青这样的大师级玉雕师,不愁学不出名堂。三年来,当学徒的他天天手摸和田玉,心中温润光洁起来,性子也变得随和。师父说,因为玉器有坚韧耐磨蚀经久不变的特性,精光内蕴不事张扬,虽亮丽而不夺人眼目的含蓄,因此,古圣先贤“比德于玉”。
师父是爱玉、崇玉、敬玉之人,他就像传说中的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冈,除了和田玉,别的玉不摸。当他的徒弟,也算是自己有资历了。可是,就在几天前,岳明手艺学得好好的,突然被叫到厂长办公室。马厂长说:“岳明啊,厂里决定调你到供销科。”
“供销科?供销科不是跑采购和销售的吗?”岳明感到很突然,我不学玉雕啦?
厂长对他说:“采购销售很重要啊!没有原料,你玉雕房拿什么雕?没有销售,你雕出来的玉器卖给谁?告诉你吧,调你去供销科是好钢使在刀刃上。跟着熊科长,好好干……”
熊科长?他脾气暴躁,拳头硬。听说,在他手底下干活的年轻人没少受虐待,来一个跑一个。
厂长哈哈大笑:“熊科长可是有大本事的人,全厂二百多号玉工全年的用料,他一个人包圆,而且拉回来的全是上佳的玉料。跟着这样的人干,你算搭上直升飞机了。”
母亲担心岳明去了受委屈,毕竟什么是供销他根本不懂。父亲却说,“我岳家的儿子不能认怂”。他只可惜儿子的玉雕前功尽弃了。
师父单常青只说了一句:“去不去由你。”
其实,根本由不得岳明。服从组织调配是一个共青团员必须做的,岳明没有二话。但他心中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让他舍不得离开师父的工房。
到供销科报到的第一天,熊科长恶狠狠地瞪着他说:“你小子是我从厂长那里好不容易要来的,不好好干,看我怎么收拾你!”
“为什么要我?”岳明是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熊科长瞪着不被理解的眼睛。
岳明无奈地笑了,“我要知道还问你?”
“笑什么笑!放你一天假,回去准备一下,后天跟我去和田。”熊科长绷着脸。
“啊?去和田?真的?”岳明恍如梦中。
科长早已不理他了,准备打电话。
岳明冲出供销科,激动地扔飞了帽子,忽又不敢相信地折回去问:“科长,你没骗我吧”。
“骗你?我摢不死你!”科长说着就要伸手打人。
岳明逃之夭夭。
和田,在岳明心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远方,他实在无从预测,那块宝地潜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危险和困扰。只知道,这个因昆仑山神秘而又美丽的地方,位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南端,玉龙喀什河和喀拉喀什河是它的生命之源,和田玉就是它的灵魂。传说昆仑山的神仙们曾把昆仑玉种在苗圃中,精心呵护一千年才能泌出一滴玉膏,然而玉非常难种,常常眼看快成膏时,一不留神前功尽弃,数百年的心血瞬间化为乌有。现在,去和田这件事,在岳明心里就像神仙种玉,他真担心这个机会稍纵即逝,美梦成不了真。
两天后,岳明如愿以偿,他唱着“光阴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从南方小城走进西北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