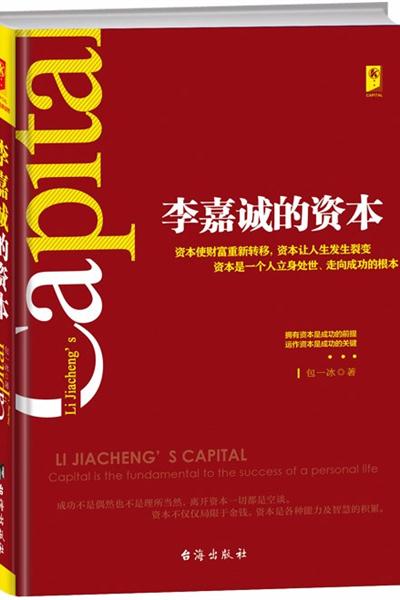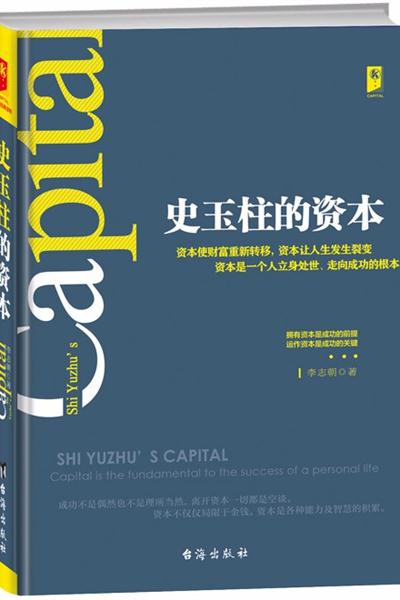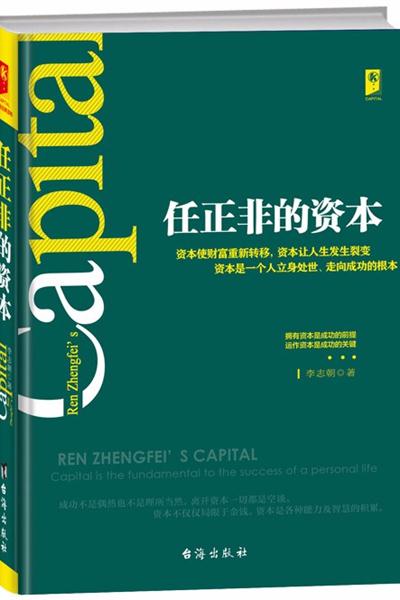国难当前,戴笠却积极扮演着反共先锋。他派手下暗杀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宣侠父;又派特务潜伏到陕甘宁边区,进行破坏活动,但效果并不显著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就是在合作期间,国民党也念念不忘对付中共。
宣侠父
西安是靠近延安的大城市,也是国民党极为重视的军事要地。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派出自己的得力干将蒋鼎文坐镇西安,而中共则任命宣侠父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
宣侠父是黄埔一期学生。早年留学日本,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能言善辩、机智过人,曾在冯玉祥部作过统战工作。蒋鼎文和宣侠父既是同乡(浙江诸暨人),又是师生(蒋是宣的老师)。另外,西安警察局长杭毅也是宣的老师,西安警署司令董钊和宣是同学,西安的显赫人物杜斌丞(陕西省府秘书长、杨虎城部总参议)、赵寿山(西北军三十八军师长、军长)等与宣交往密切。正因这些有利条件,中共派宣侠父来西安协助林伯渠工作。
宣侠父一到西安,戴笠即令军统西北区区长张严佛严密监视其在西安的一举一动。
张严佛指示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李翰廷在八路军办事处门口加设了一个警察派出所作为固定监视哨,重点监视宣侠父。张严佛严格规定:
派出的对付宣侠父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都以穿警察衣服的公开身份,在指定的范围内,作固定的监视,不化装、不离开派出所岗位,不作流动侦察和跟踪;对宣侠父和其他人的监视,必须绝对秘密,不得向任何人泄漏,否则以泄漏秘密论罪。固定监视宣侠父的主要要求是:确实掌握宣在办事处的居住和行动,如有迁移或离开西安的迹象,必须立即报告。另外,张还指示两三个精明狡猾的特务专对宣侠父轮番跟踪,流动侦察。
从1937年冬天起,戴笠根据西北区的情报,不断向蒋介石汇报有关宣侠父的活动情况,主要内容有:宣侠父在西安与杨虎城旧部杜斌丞、赵寿山以及赵寿山派驻西安办事处长老共||产党杨晓初等,来往勾结,教唆杜斌丞、赵寿山等反中央、反蒋;宣侠父与西安各方面左倾人物广泛接触,打着抗日救亡的招牌,煽动西安学生、流亡青年到延安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宣侠父所在地成了左倾人物、青年学生聚散的中心,因此引起西安各学校学生思想混乱,学生不安心求学,学风败坏;宣侠父在西安以黄埔同学关系与机关、部队军官拉关系,散播共产主义思想毒素,影响所及,势将引起军官思想动摇,部队叛变;宣侠父在西安“公开指责中央,诽谤委员长”,谴责委员长限制言论、出版自由,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歧视共||产党、不补充八路军武器军用品,宣侠父散布不利于中央和破坏抗战的言论;宣侠父在西安指挥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等等。这些情报内容空洞,没有具体事实根据,但引起了蒋介石对宣侠父的仇视,急欲除之。
1938年5月,张严佛调到武昌军统局代理主任秘书,跟踪监视宣侠父的任务改由徐一觉负责。
6月底,蒋鼎文接到蒋介石指示杀害宣侠父的密电后,亲自下了一个手令交给徐一觉。手令内容为“派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将宣侠父密裁具报,蒋鼎文(签名)”。徐找来李翰廷、李良俊等特务商量具体行动方案,为确保秘密,决定深夜在城内动手。
因为宣侠父的行动无法掌握,徐一觉要求蒋鼎文帮忙。某夜11时后,蒋鼎文打电话给宣侠父要他立即到自己的住处后宰门公馆(距离八路军办事处1公里),有要事相商。宣侠父只觉事有蹊跷,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几天前延安中共中央曾发来密电,称蒋介石已有杀宣侠父之心,很可能会在最近动手,让宣侠父择机离开西安。宣侠父何尝不知其中的危险,但自己的工作关系更多人的安危,他不忍离去。宣侠父放下电话,旋即赶往后宰门公馆。
死亡已一步步逼进!
谈话直到和徐预先约定的凌晨1时左右,蒋鼎文才让宣侠父回去。待宣侠父走到预定地点,徐一觉轻轻挥了挥手,特务李翰廷、李良俊、张志兴悄悄地跟了上去,迅速将宣侠父架进已准备好的汽车里,用棉花塞住嘴。李翰廷、徐一觉同时下手抓住宣侠父的咽喉,套上绳索,两边拉紧,宣侠父怒目圆睁,终于停止了呼吸。
李翰廷伸手摸了摸宣侠父的鼻子,说:“还算顺利。开车,到下马陵去!”
下马陵是西安偏僻的地方之一,附近没有老百姓住宅,白天都没人来这里。徐一觉早已命令几个人在这里放哨警戒。汽车一到,立刻把宣侠父的尸体抬下来。徐一觉伸手在宣侠父身上搜出一块金质怀表和一条黄金表链,他放在嘴里咬了一下,试了试成色,随手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把宣侠父的尸体扔进枯井。
一代英雄宣侠父,陈尸井底。
第二天,徐一觉当面报告了蒋鼎文,蒋发下了奖金2000元,徐自己独得1000元。
不久,延安共||产党知道了宣侠父的死讯。林伯渠向蒋鼎文提出抗议,要求缉拿凶手。蒋开始推作不知,只答应查询,实则敷衍搪塞。同时,命令李翰廷等人把宣侠父的尸体移到城外一个离道路较远的荒地埋起来。当时军统局西北区已经由西安新城搬到东南隅玄枫桥仁寿里四号,离城墙近,就在城墙根挖了防空洞,开了两个口通向城外,加设了两道门,平时上锁,遇到日寇飞机轰炸,可从防空洞里面疏散到城外去。宣侠父尸体迁移后,丁敏之领张严佛到城墙上,指着西安城外东南角上离城500米的新土堆向张严佛说:“宣侠父尸体就埋在那里,从防空洞搬出去的。”
不久,参与暗杀的特务徐一觉、李翰延、李良俊等因分赃不均,泄露秘密,林伯渠以此为线索,一追到底,并向社会公布了此案,引起西安左派人物及社会进步团体的同声谴责。蒋鼎文无奈,只好请求中央出面解决,迫于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向周恩来表示:“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背叛了我,是我下令制裁他的。”
戴笠对付中共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派特务潜伏到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进行破坏活动。
戴笠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依靠设在榆林的陕北站(站长黄逸公)和设在关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戴笠命令黄逸公、程慕颐在被扣押的青年学生中,挑选部分可靠分子(出身较高或国府党政军官员的子弟),经过一番短期培训,再以进步学生名义,混入延安。当时中共中央社会部对进入延安的学生的办法是:来者不拒,动辄必究,自首者欢迎,为恶者逐出。这套办法使打入延安的数百名“骨干”,大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少数人搞了些情报,但很快被边区政府查获遣送回来,并拿着他们的交代材料,向国民党当局方面问罪。
戴笠见此计不灵,干脆以冒名顶替的方法,直接派“军统”骨干拿着没收学生的各种证件,混入延安,比较知名的如袁良、赖国民、沈之岳、秦文礼等,他们在延安潜伏了一段,只是始终没搞到比较有价值的情报,后来因吃不了苦,或害怕被问罪都相继离开边区。戴笠自欺欺人,专门召开座谈会,让这些“延安回来的人”,讲述潜伏边区的方法和体会。
遗憾的是,他们只讲了“说难道易”六句话:“打入容易立足难,潜伏容易活动难,个人行动容易,组织串联难,一般应付容易,取得信任难。”把这几句话总结一下,就成了:打入、潜伏、个人搞些小动作比较容易;真正站住脚,搞活动、建立组织,根本不可能。这种结论,显然是失败的结论,戴笠当然不死心。正在日夜寻思,枯肠搜尽之际,张国焘的点子又启发了他的灵感。
张国焘于1938年4月自陕北叛逃到武汉,后被蒋介石召见,加封为中将、国民参政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反共设计委员会主任秘书、军统局特种问题研究室主任。
张国焘到军统后便帮助戴笠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圹举办了“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反共特工。“怎样打入边区去”是训练班的一门重要课程。张向戴一再吹嘘,经他训练出来的特工,对边区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以及党政军建制、施政方针、工作方法等,都有透彻的了解,让他们搞策反万无一失。在张的鼓动下,戴笠便在汉中、洛川、耀县建立了三个“策反站”,先后向边区派遣特训班特工一百多人,活动结果仍然不理想,不是被中共方面抓住把柄遣送而回,就是搞来一些过时情报,毫无使用价值。张国焘的声誉由此而一落千丈,座上宾变为奴下奴,最后,不得不到歌乐山附近河塘,靠养鸭卖蛋维持生计。
中共在军统局的无线电台有了自己的特别小组,中共无线电英雄张露萍打进军统电讯总台,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戴笠费尽心机逮捕了张露萍,严刑酷法也逼不出口供
抗战中,国共双方较量的另一个阵地就是无线电台。中共的“楔子电台”直接打进重庆军统中枢,活动阵地就在军统电讯总台。这对于“特工王”戴笠来说,简直是个莫大的讽刺。
“楔子电台”的主要负责人是“牛角坨七人小组”。
“七人小组”的组织称谓是“中共军统局电讯总台特别支部”,支部书记张露萍,其他成员有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陈国桩、王席珍。张露萍当时只有19岁,她是四川崇庆县人,本名余家英。余家英姐妹三人,她居“老末”,自幼聪颖好学。10岁时,入成都东德小学,14岁考入刘文辉创办的成都市建国中学。1935年年底,北平学生发动了震撼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成都各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响应。余家英在学联的组织下,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分裂。
“民先队成都队部”成立后,余家英成为首批“民先队”队员,并在建国中学“民先队小队”中,负责宣传、组织工作,她就像初次凌空的雏燕,不知疲倦地扑腾着双翅,时而写墙报,时而做演讲,时而指挥唱救亡歌曲,时而化妆登台演出……她第一次感受到投入革命洪流的荣誉感和幸福感。
1938年2月初,余家英化名黎琳,被“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护送到了延安。黎琳先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二期14队,学习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等课程。短训班结业,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由于她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工作学习都很认真,被选为班级活动小组长,每逢学校集中上大课时,经常指挥大家唱歌,尤其爱唱那首拿起刀枪干一场的歌,久而久之,人们便亲切地称黎琳为“干一场”,后来竟成了她的代称。1938年10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干训班,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第二年,组织上考虑到黎琳和川军上层人物(指其姐丈李安民)的关系,派她入川工作。
张露萍
黎琳到重庆后,立刻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到。当时,国民党刚开完中央全会,正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各地方都由“政治防共”改为“军事反共”,作为特务大本营的军统局,也在千方百计搜捕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了准确地掌握敌人动向,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已在军统局电讯总台发展了两名内线党员——张蔚林和冯传庆,只是人单势孤,开展工作受到局限。根据周恩来意见,叶剑英找黎琳谈话,准备要她打入军统电台,作为一个楔子,钉在军统局中枢线上。黎琳没有犹豫和推托,完全接受组织的安排。
为了迅速接近军统电台,组织上又让黎琳化名张露萍,成为张蔚林的妹妹,来重庆补习谋职。军统局规定,内勤机要人员有家属的可以住进牛角坨宿舍。为了照料“妹妹”生活,张蔚林申请到了一套房子,“兄妹”俩组成“家庭”。张露萍根据工作需要,从发式、化妆、穿着、行动作风等各方面,完全按一个活泼、文雅、摩登的女学生来设计。中共南方局给她明确的任务是:负责传递张蔚林等从军统局搞到的情报;成立军统电讯总台特别支部,张露萍为支书,要积极发展条件成熟的青年入党,壮大组织力量;直接接受南方局军事组的领导,不与其他组织发生横的联系。
1940年春,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展到顶峰,在北方前沿,胡宗南侵占了陕甘宁边区5个县,阎锡山发动了晋西十二月事变;石友三、朱怀冰部进犯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在大后方和国统区,则实行白色恐怖,动用大批军警宪特,捕杀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在这关键时刻,张露萍的特别支部发挥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特殊作用。军统局通过电台发出的一切密令、行动计划、搜捕安排,都一字不漏地及时传送到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在对敌斗争中,争取了主动。
1940年2月,戴笠和胡宗南勾结,由重庆直接派出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着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区搜取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中共的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同年4月,设在天官府街十四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更多地抓捕共||产党人。这个情报送来的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让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坨,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
军统破坏地下联络站的计划落空了,戴笠却从中产生了疑问,为什么我的秘密行动走漏得那么快?为什么中共的准备又是那么充分?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通敌?想到此处,他倒吸一口冷气,好厉害的共||产党,竟然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眼线。消息焉有不漏之理。
戴笠情急,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之处,一律先拘后审。
事出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顾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焉有不担心之理,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去省亲。
不料在此期间,张蔚林出事了。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关系不好,想借机报复一下,便说张是有意破坏,就把张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返回军统局,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
张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七人小组的名单。等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立即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军统电讯台大院,跑到“八路军办事处”来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已在返渝途中,无法补救。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牛角坨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这么严重的案子,使戴笠又气又恨,又有点无地自容。他要亲自审理此案,按照他的估计,这七个青年背后,定有大人物在指挥,如果找到突破口,反共又会多一张王牌,在老头子面前,还可挽回一点面子。但他没料到,这七个年轻人竟是这样棘手。
戴笠先审张露萍。他认为,一个19岁的女孩子没有多大能耐。戴问:
“你叫什么名字?”
“张露萍。”
“有没有别的名字?”
“没有。”
“胡说!那余家英是谁?”
张露萍察觉,军统一定在成都作了调查,了解了自己的身世。心想,正好以此来做掩护,答道:“那是我的学名。”
“你去延安干什么?”
“抗日呗!”
“在抗大受过训吗?”
“受过。”
“共||产党派你来重庆干什么?”
“不是派,是我自己偷偷回来的。”
“胡说,你还想赖!”
“我受不了延安的苦就跑回来了。”
“你不回老家,来重庆干什么?”
“我没脸见父母,想在重庆补习功课考上大学再告诉家人。”
“为什么和张蔚林称兄妹住在一起?”
“我们在谈恋爱,因为你们军统有规定,机要人员不许和外人谈恋爱。”
戴笠自感无懈可击,只好改用老套活。不说真话,就用刑。
掌嘴、钢丝鞭、钉竹签、下夹棍,张露萍体无完肤,但还是没有招供。
对张蔚林等其他6人的审讯,也是如此。
后来,戴笠故意把张露萍放出,派人跟踪,张知其用意,几次路过“八路军办事处”看都不看一眼。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7人死刑,报蒋审批。蒋介石还想以7人为反共凭证,遂批为“死缓”,囚禁在白公馆。1941年3月,张露萍等七人小组,被转送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夏,戴笠视查息烽集中营时,忿忿地对集中营主任周养浩说:“现在放着他们还有何用,闹不好在狱中还要生事,干脆秘密除掉算了。”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7位勇士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从军统与其驻西安办事处的来往密电中,毛泽东摸清了蒋介石的底牌,毅然赴重庆参加谈判。戴笠寻机对毛泽东下毒手,最终毛却安然归去,戴笠只能望洋兴叹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形成“一山二虎”之势。当时,国民党主力部队正在西南、西北地区,难以在短期内调往各地战场,因而战略态势对国民党极为不利。蒋介石为争取时间备战,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谈”,“共商国是”。
蒋在陪都重庆所发的每一封“诚挚”的和谈邀电,都马上刊登在国民党的各大报刊上,彰显出一副殷殷期盼的样子。其实,蒋介石的真实目的,说白了也就是“假和平、真内战”,毛泽东对此早就料到了。
但是,当时的情形并不简单,在接到蒋发来的电报后,中共和毛泽东开始积极紧张地寻求对策,在重庆与延安来来回回的电报之间展开揣摩与斗争。
对蒋的第一封电报,毛泽东没有马上回复,到16日才回函蒋介石:“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而且尚未表态是否一定会赴渝。同时,告诉李克农说:“蒋介石发电报要我去‘和谈’,并不意外。七大上我就说过:谈是要谈的,但他们不会有诚意,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也没有。不过,人家已经发了邀请,我们能不去?现在,关键是要尽快搞到具体情报,证实一下我们的判断,摸摸蒋介石的底,看看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毛泽东将弄清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李克农。李克农可不简单,他虽没有领过兵,没有打过仗,但却是一位将军,是中共情报史上的风云人物,被誉为“龙潭三杰”之一,与戴笠算是一个职业!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据说,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获悉李克农去世的消息后,居然欣喜不已,宣布休假3天,以庆贺强有力的对手消失了。这个举动在中央情报局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由此可见李克农的能力与声威了。
李克农
当时李克农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专门负责领导和指挥中共的情报与政治保卫工作。接到毛泽东的指示之后,李克农便迅速组织情报系统,不分昼夜地忙碌起来。他的情报系统日夜监听国民党的电讯,想捕捉信息。但国民党使用的密电电码无法破译。他忽然想到国民党在延安驻有联络处,必定与重庆就毛泽东是否接受邀请有密电往来。
李克农很快把注意力放在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身上。他深信,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定会密令周励武、罗伯伦收集延安方面的情报以作出相应之策,因此从他们的来往密电中可以弄清蒋介石此举的目的。
8月15日晚,李克农从情报部门获悉:重庆各报已被告知,第二天一早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电报。李克农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蒋介石看我沉默,便展开舆论攻势。我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次日,毛泽东发出给蒋介石的回电。电文很短,回避了他是否要去重庆参加谈判的问题。电文发出以后,毛泽东接见了周励武、罗伯伦。周励武询问毛泽东对蒋介石来电的看法。毛泽东当面告诉他们先不准备去重庆,等蒋委员长答复电报后,再作考虑。
得到毛泽东的回答以后,周励武忙向重庆汇报了自己会见毛泽东的经过,明确告知:毛泽东绝不会去重庆。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回电和周励武的“第一手情报”后,忍不住说道:“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绝不敢来重庆。”
李克农严令情报部门,严密监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动向。当周励武在延安将所谓情报发给重庆,送到蒋介石手中时,就会有同样一份情报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了一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电文很长,口气强硬。李克农在拿到电报后断定,蒋介石这是假戏真唱,其实他绝不希望毛泽东去重庆与他谈判,而是估计到毛泽东不敢去重庆才故意逞强。蒋介石想假戏真唱获得舆论上的优势,毛泽东不去,他就可以把拒绝和平的责任推到共||产党头上。这一招不可谓不毒。李克农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分析后,毛泽东决定再给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增强他的错误判断。8月22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了第二封电报,并再次接见周励武、罗伯伦。一见面,毛泽东就“开诚布公”地对周、罗说:“蒋委员长的电报已收到,我已复蒋委员长,因自己工作繁忙,无法脱身,为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庆与蒋会晤,待恰当时机再相机赴渝。”
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第二封回电后,心中暗喜:果然不出所料,毛泽东被逼无奈,派周恩来到重庆与我周旋,自己则躲在延安不敢露面。蒋介石更是决心把这场假戏唱到底了。他要把毛泽东、共||产党推上承担内战罪责的被告席。
8月23日,蒋介石给毛泽东发去了第三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毛泽东收到电报,大笑不止:“蒋介石要把假戏唱到底喽!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
8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毅然决定亲自率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戳穿其假和平的把戏。
李克农感到自己责任重大。毛泽东决定亲自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主要依据就是十多天来他提供的情报和分析,如稍有偏差,可能会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使党和人民利益遭受巨大损失。为此,李克农又反复核对了收集到的情报并再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这场情报战是该收网的时候了。李克农下令封锁消息,不让国民党得知任何关于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消息。
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准备工作在高度保密下进行着,而国民党特务周励武、罗伯伦却懵然不知,在重庆的蒋介石则更是两眼如盲。
8月26日,蒋介石在得到周励武密电,报告毛泽东不会来重庆的情报后,得意地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派一“大员”乘飞机去延安接周恩来,同时再次当面邀请毛泽东来渝。8月28日上午,在延安的周励武、罗伯伦又提出会见毛泽东的要求,中共方面婉言回绝:毛泽东正与同国民党“大员”一起来延安的美国大使赫尔利等人谈话,周恩来下午将乘飞机与赫尔利等去重庆。得此“情报”的周励武、罗伯伦,又一次向重庆发出密电,称毛泽东无意去重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当这封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中时,毛泽东已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登上了赴重庆的飞机。李克农看到破译出的周励武发给重庆的密电时,不由得开怀大笑。
8月28日,当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出现在重庆机场时,蒋介石、戴笠二人目瞪口呆。蒋介石自叹在谈判开始前,就在政治上打了败仗。戴笠自知失职,当毛泽东在机场频频向欢迎者含笑致意时,他却惊慌地赶到蒋公馆商量对策。
毛泽东与赫尔利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戴笠试探地问了一句:“毛泽东到重庆,我们军统该干些什么?”
蒋介石断然道:“千万不能胡来,否则影响太大,对我们不利。我想安排毛泽东住在曾家岩桂园。雨农,你要好好地保护我请来的客人啊!”
戴笠会意,领命而去。
戴笠把由宪兵特工组成的警卫班安排在桂园左角一小屋内。这间小屋可一眼看到整个桂园,而且隔壁有美军总部宪兵排的军用电话,可以随时与外界联系。
戴笠规定警卫班成员一律不能回家;要严格遵守纪律,对违反纪律的,一律按军法处置;任何人都不许接近毛泽东。
戴笠唯恐不周,又特地吩咐一名武装宪兵站岗,另外两名宪兵担任毛泽东外出的随车警卫工作。
“除朱副官(毛泽东警卫队副队长朱友学)准许进出的人和介绍给我们认识过的人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进入。”戴笠特地强调。他想:“这样可以切断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同时,戴笠并不死心,仍然想乘机搞些情报:“我搞军统几十年,成立西北工作站,几次派人打进陕甘宁边区,总是一无所获,现在毛泽东就在自己眼皮底下。我一定要趁此摸一摸共|产党的老底。”
戴笠指定一人专写情报日记。约定在情报日记中称毛泽东为“何先生”,朱副官为“老吴”。具体内容为:
(一)何先生今天×点××分到18号(毛住宅)。
(二)上午×点有某人(男、女或外国人,相貌、身材、服装、年龄)到18号,于×点×分离去,老吴做××。
(三)中午何先生赴××宴会(写明请客人的姓名地址)。
(四)下午何先生接见××××人,又到××街访友。
戴笠亲自过目后,交给内勤宪兵,然后由特高组派人伪装“传达兵”来桂园取走,连同其他方面的“日报”,择要摘编,报告蒋介石。
可是戴笠丝毫没有得到任何情报,苦恼极了。一个警卫特务见状,忙堆上笑脸,献计道:“为什么不乘机会把毛泽东除掉?坐上几年牢便可立大功了。”戴笠气得狠狠地就是几个巴掌甩了过去。打过之后,戴笠一惊:“如若有谁做亡命之徒,这岂不是军统闯祸了!”戴笠越想越惊,便又在桂园增添了一个游动岗哨!
1945年10月10日下午6时,国共双方代表在会谈纪要上签字,11日上午9时,王若飞偕毛泽东等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启程飞回延安,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留在重庆,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戴笠望着渐渐起飞的飞机,心里颇不是滋味,他感叹道:“我一生在和众多的对手较量中,很少输过,可这一次不仅什么都没捞到,而且担惊受怕整整43天!”
10月11日下午1时30分,戴笠收到毛泽东平安回到延安的情报!只好望洋兴叹。
抗战爆发后,“军统”与“中统”正式分家。戴笠在军统局虽只是副局长,却实权在握。他总结多年经验写成政治侦探,提出了特务内部管理方式,成为“特工王”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特别强调抗战期间,必须加强特务统治。他决定在取消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基础上,设立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1938年8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改组。中统局由徐恩曾任副局长,军统局局长由贺耀组兼任,戴笠任副局长。贺耀组只是挂名局长,军统大权由戴笠独揽。
戴笠当上了军统局少将副局长,手握实权,野心勃发。他开始著书立说,编写特工教科书,以期来教育、启发“子弟兵”。
春风得意时的戴笠
1939年,戴笠撰写了实用的特工大全——政治侦探。在本书中,戴笠从理论上论述了特务工作的性质和职能。他指出特务不仅仅是进行绑架、逮捕、暗杀的打手,而且是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一支特殊力量。戴笠在书中指出机密是特务工作的最重要的特点。特务是“以绝对秘密之身份,受独立组织之指挥”,其组织、身份、工作都十分机密,“视上级命令之所指派,分驻各处,严密注意当地一切关于党,军,政,学,工,商人民之动态。凡有贪墨奸污,借公奉私,足以祸国殃民之事端,以及违法抗令,暗蓄异志,足以形成反动阴谋之行为,均须以最机密、最迅速之方法,洞悉内情,以最忠实,最正确之报告,摘发制裁。”
戴笠指出保卫领袖的安全、惩办一切贪污不法、扑灭一切反动势力、协助国家建设、防制国际间谍和扑灭汉奸这五个方面,是特务工作的主要任务。戴笠还将特务工作方式分为“情报”、“煽劝的破坏”、“行动的破坏”三种,并对每一种工作方式和手段都进行了系统阐述。
戴笠仍然十分重视纪律问题,在政治侦探中,戴笠特设“政治侦探之‘铁的纪律’”一章,专门阐释这一问题:“政治侦探不仅在工作上应遵守团体之‘铁的纪律’,而且在私生活方面,亦须受纪律的约束,如有违反纪律者,为顾全大局计,为爱护工作人员前途计,自应予以劝导或惩戒。”
在书后,戴笠附有政治侦探法草案,严格规定了政治侦探中的犯罪行为及其惩处判刑的方法,如:
第十七条预备或阴谋危害党国者,处死刑。
第十八条预备或阴谋危害最高领袖者,处死刑。1941年“四一大会”戴笠题词
第十九条预备或阴谋危害政治侦探最高负责人者,处死刑。
……
第三十九条私擅集结小团体者,依下列各款处断:
一,首谋,死刑或无期徒刑。
二,余众,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在草案中,戴笠还详细规定了抗命罪、渎职罪、贪污罪、诬陷罪等罪行的处罚办法。
不久戴笠进一步提出“主义领导,理智运用,感情结纳,纪律维系”的十六字方针,指导军统工作。戴笠认为在实际工作中,与部下之间除要加强感情联络外,还要严肃组织纪律。为做到这两点,戴笠大念“官”、“管”、“棺”三字经,即对特务:先给“官”做,若贪污枉法,则改为“管”;若违命抗尊,则改为“棺”。
在戴笠制定的许多禁令中,最有名的是“六不准”,即:不准擅自脱离组织;不准在抗日时期结婚;不准自由向外活动;不准经营生意;不准贪污贿赂;不准随意回家外宿。但这些规定多是对下不对上。
在强调“硬”的一手的同时,戴笠也善于用“软”的一手。他常说“同志如手足,团结即家庭”。戴笠笼络部下的方法主要有:关心特务的生活和前程;恩威并用;在与外界争斗中,包庇部下;鼓励“集体主义”,提倡“同生死,共患难,同甘苦,共荣辱,只有团体没有个人”。他还规定,从1940年起确定每年四月一日为军统创业纪念日,并于这天召开隆重的“四一大会”,把祭祀死难者作为大会的首要程序。戴笠这套制度十分严密,他也被人称作“特工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