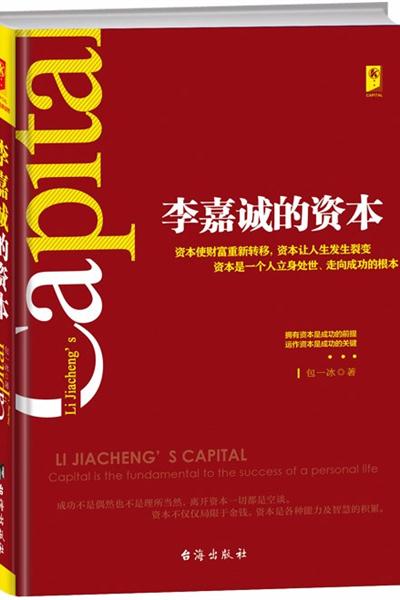谭延闿出生于浙江杭州,长于官宦之家,父亲官至清朝总督。深厚的家学渊源和父母亲的双重影响,无形中培养了他的精神品性,初步奠定了他建德立功的基础。
谭延闿,祖籍湖南茶陵,1880年1月25日生于浙江杭州(其父时为浙江巡抚),字祖安、组庵、祖庵,别号慈卫,亦号畏三、无畏,后改名为延闿。之所以改名缘于其父对湘潭大学者王闿运才学的推崇,也正因为此,后又让谭延闿拜于王闿运门下,读书习作。
谭延闿出身书香名门,其祖父谭恒从小喜好读书作文,长大后在湘潭一带教私塾,为人豁达忠厚,被人誉之为“九淘先生”。其父谭钟麟在四兄弟中排名第三。谭钟麟少年时家徒四壁,生活拮据,常常“不能供粥”,以致在16岁那年就辍学养家,但现实的苦难并没有摧垮谭钟麟积极向上的心,他常常白天工作,晚上就在寺庙研习诸子百家的作品,并时常请教于当时的学者名流。谭延闿曾在先府君行状回忆父亲的这段经历:父亲“年十六,即授徒自给,已乃发愤读书。山寺习诵,常至夜分。所处绝困厄,非人所堪”。
谭延闿
然而皇天不负有心人,几十年的挑灯夜战换来的是一次次的高中:1843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秀才,进入了州学;继而又在1849年的乡试中高中举人;于1856年会试中进士,进而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1859年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江南监察御史、杭州知府、河南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浙江巡抚、陕甘总督、吏部左侍郎、闽浙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可谓是晚清政坛上的达官显贵,仕途通畅,官运亨通,成就了其名利鼎隆的一生。
在谭延闿的生命中,其母的影响可谓十分重大。其母李氏,系河北省宛平县人,原是谭府的丫鬟,后由于谭钟麟的原配陈夫人患病,谭钟麟听闻李氏贤惠聪敏,娶其为妾。由于庶出的地位与身份,在讲求封建礼仪的谭家,其待遇与尊严可想而知。
据记载:全家吃饭时,大奶奶、二奶奶舒服地坐在那里吃,她只能站在一旁服侍她们,待她们吃完后,她才可以上桌吃饭。大家因此也就叫谭延闿“小老三”,只是后来由于谭延闿高中会元,其父才向家里人宣布,“李氏夫人可以入正厅就座用膳”。大家也不叫谭延闿“小老三”,而叫他“三大人”了。前后称谓和母亲地位的变化,使谭延闿惶恐不解,于是他就带着这个问题问自己的母亲,于是,母亲眼中带泪地解释道:“我是你父亲的小老婆,有些人把你们兄弟称作‘小老三’、‘小老五’,除了年小的缘故外,还带有‘庶出’的意思。你们兄弟要努力读书,好好做人,将来做番大事业,做个大人物,才算是争光争气,那我在谭家虽然吃苦也感到安慰了。”这无形中培养了谭延闿对封建等级制的不满。
正因为对母亲遭遇的深切体悟,在他后来老婆方氏病逝后,即使他正当中年,最该有个女人照顾,即使由他最崇拜的孙中山亲自做媒介绍的是留美归来的宋美龄,可他“以不能背了亡妻,讨第二个夫人”为由坚持不再娶,坚守和其妻子的诺言,把几个儿女带大。母亲不幸的遭遇和惨淡经历从小赋予了谭延闿委曲求全、察言观色、圆滑机智、小心行事的精神品格,更铸就了他不屈不挠、为母争光、光耀门庭的精神动力。
母亲对谭延闿最大的影响是对其的教育。母亲经常教导他们:“读书就是为了学做有用的人,仅仅只是猎取富贵有什么益处?我希望你们做一个有用的人,不希望你们获得一个好官职。我服侍你们的父亲走遍各地,久知做官的难处。官位低下的人往往不能阐发自己的志向,官位尊贵的人又很难得到人心。我亲眼看到你们的父亲早起夜思,不敢有一息自我安乐,即使这样,还是感叹自己想做的事不能尽情进行,进行的事又往往不尽如人意,何况那些职位低的人?你们的才识远不及你们的父亲,就做管理老百姓的官,这是我为你们感到忧虑的。”又说,“人们依靠富裕的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在人们危急困难时给予解救。如果富裕的人只顾自己聚敛钱财,那么有什么可贵的呢?”
母亲对做官之道,对做人之则的解读,对谭延闿养成忠敬敦厚、同情弱小、雍容有度的性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做了许多事孝敬其母,不仅以“慈卫”之号自称,并著有慈卫室诗草以示对其母的纪念,而且由于“庶出”隐痛,坚持不续弦,更是出于对母亲的敬仰和尊重,大力赞助新式教育,声称:“吾幸者,母子同心,吾出赞助教育,实秉吾母李太夫人命”,在第一次“被迫”主政湖南时,虽然“惊悸失色”,仍然称“奉母命而维持秩序,以免地方糜烂”,毁家纾难、变卖家产为孙中山筹措军费,资助孙中山革命更是源于母亲的支持和理解,以致在母亲去世时发出“母竟不待天乎,痛哉!”的感慨。
还有一事值得一提,谭家家风谨严,非正室的灵柩不能从正门抬出,谭延闿力争母亲的尊严和待遇,仰卧于灵柩之上,大喝“我谭延闿已死,抬我出殡”,族人顿时面面相觑,无人吭声,也无法阻挠,只得让灵柩从正门抬出。这就是有名的“卧柩出殡,孝满天下”的故事。
总之,出身于官宦之家、簪缨之庭的谭延闿,由于渊源的家学,从小就跟随父亲治学做人,求取功名,母亲的贤明敦厚和不幸遭遇无形中影响了他的人生志趣和价值追求。同时,作为总督之子,这种显赫的身份和地位为谭延闿迅速在科举之路崭露头角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谭延闿聪颖好学,在随父亲南北做官的游学生涯中,受教于各地巨儒名师,很快便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成为湘人有清200余年来第一个会元。
谭延闿虽然是官宦子弟,但并不骄横,聪颖好学,自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勤学苦读,7岁开始就入私塾读书,11岁学制义文学,光绪十八年入府学。在众多的兄弟中,父亲认为他是个读书的好苗子,被帝师翁同龢称为“伟器,笔力殆可抬杠”,这更使父亲注重对其的口授言教。
谭延闿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跟随父亲南北做官的生活中度过的,这种生活和经历带给他的是生活阅历和见识的不断增加,是对社会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同时也对他的待人处事和治世服官、进德立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每到一处任职,谭钟麟都为儿子寻访名师,对其严加教育和监督,这既源于谭家的家学,也源于谭延闿的聪颖好学。谭延闿出生后,其父就从浙江巡抚调任陕甘总督,直至7年后由于眼病而离职。在这7年中,谭延闿在兰州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他的启蒙老师是兰州的张宝斋。张老师是一位“喜谈字学”的饱学之士,经常给谭延闿讲古今的有趣知识,深得谭延闿的喜欢,直至多年后,他都对老师记忆犹新,在儿时杂忆诗中回忆道:“霜鬓庞眉一尺须,万言撑腹注虫鱼。熏笼围坐听闲话,更乞先生为甚酥。”后又受教于姚世贞、李少苏等人。
随后谭钟麟调任闽浙总督,谭延闿随至福州,先师从陈春坞,后又受教于谭铭三,在福州居住期间,谭延闿曾返回长沙参加了童子试和乡试,后于1895年随其父到广州,受教于丁伯厚,这位老师也给谭延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先生谨身慎行,躬行实践,下笔不苟,勤勤不稍假借。今日读此,犹见循循善诱之衷,至为可感。”在广州期间,谭延闿又回湖南参加应试,以第二名得好成绩荣登大榜。
由于父亲1899年乞假返乡,谭延闿随之回湖南。在湖南,他于1902年在长沙参加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本省乡试,中试为第九十九名举人。1904年3月,谭延闿前往开封参加甲辰科会试。由于八国联军的入侵,北京的贡院被毁坏,一直未能修复。因此,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只好在开封贡院举行。在这次考试中,谭延闿高中第一名贡生(即会元),成为清200余年来湖南第一个会元,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会元。谭延闿一朝高中,整个三厢为之震动,轰动了朝野政坛,湖南巨儒王闿运特写文章叙述此事,“看京报,文卿儿得会元,补湘人二百年缺憾,龚榜眼流辈也”。陈锐在碧斋诗话中也记载道:湖南会元,仅谭一人。辞章本其所长,独喜言经世之学,诗文鲜有存者。
4月,谭延闿又参加了殿试,以二甲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一名,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与父亲同为翰林,一时传为学苑的佳话,声名远扬。
受教于各地名师的优越条件自然有助于谭延闿仕途的顺畅、官运的亨通,但随父亲转徙南北的经历,无形中增长了谭延闿的见识和阅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个道理,在游学过程中,谭延闿既了解了各地的风情民俗,又深深体会到下层民众的苦难和不幸。这些无疑都是成就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同时,各地不断发生的政治风潮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成为诱发其思想转变的土壤与条件。
此外,父亲的为人之道和做官哲学对谭延闿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如谭钟麟在杭州知府任内,就积极着手清理赋税,减轻农民负担;督治海塘工程,疏浚长安河道,恢复农业生产;安抚流亡百姓,处理多年积压案件,整顿监狱秩序,深得百姓拥护。他在陕西巡抚任内就兴办学校、创立书局,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疏浚郑白渠,教民种桑养蚕,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解除不许回民出城的禁令,设立专门处理回汉争诉的部门,减轻了民族隔阂,赢得了回民的广泛赞誉;在陕甘总督任内立官车局,罢苛捐杂税;在两广总督任内整饬吏治、严禁赌博。他在历任之内,都力求节俭、整理财政、减轻民负;保境安民、积储仓谷、以备灾荒,诛强扶弱,赈灾济民,省察民众疾苦,颇有政绩,深受百姓爱戴和拥护,在贫瘠和偏远地区尤甚。凡此珍贵的见闻与体验,也不是其他人等所可以幸致的,自然对少年时期的谭延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照常理说,谭延闿作为书香门第出身的官宦公子,外在的优越条件加上内在的努力,使他本应该照中国传统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登上科举制的高峰,在中国政坛上一展拳脚,但是此时的中国却在发生着意想不到的重大变迁。
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沦落,刺激和惊醒了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他们为挽救国家的危机和民族的灭亡,提出和践行着一系列的主张,其中既有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之策,也有民主革命派的彻底革命之主张,二者的相互激荡构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震撼着谭延闿。就当时的思想发展水平而言,维新思潮和立宪救国体现了时代变迁的主流。而谭延闿的家乡湖南恰是维新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之地,维新斗士谭嗣同又是谭延闿的湖南同乡,相同的“高干子弟”(谭嗣同之父谭继洵与谭延闿之父谭钟麟是至交,二者的关系非常要好)身份使他们非常投缘,相交甚密,经常在一起商讨时事,共议时艰,他们二人再加上陈立三并称为“湖湘三公子”。
从谭延闿保存的谭嗣同的手札、笔记以及所作的后记就可以看出二者非同寻常的友谊:“复生(谭嗣同的字)慷慨喜谈论,意气发舒,见人一长,称之不去口,自谓学佛有得。余于戊戌七月初四过天津与林敬谷饮酒楼间,隔座叹息曰:‘有君无臣,奈何?’窥之复生也。亟呼入,与敬谷不相识,余为之介,高睨大谈,一座尽倾,明日别去,遂及于难。临刑神采扬扬”,又说:“复生自命学曾子,余乃闻其志事,戊戌七月别于天津,遂永诀矣。”字里行间对谭嗣同的敬仰和惋惜之情可见一斑。正是由于这位挚友之死对谭延闿的触动以及社会上暗自涌动的反清潮流,使这位士大夫逐渐脱离了封建卫道士的营垒,渐渐走上了反清的道路。
谭延闿初涉政坛,积极兴办新式教育,资助和支持明德学堂,任湖南省谘议局议长,积极保护路权、争取利权,堪称立宪运动的先锋,立宪派的领袖。
1905年3月12日,谭钟麟病逝于长沙,清政府追谥“文勤”,追封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谭延闿报了丁忧,回乡为父亲守丧。时值清政府实行所谓的“新政”之时,谭延闿的家乡湖南也开始推行新式教育,建立新式学堂。“据统计,至1905年止,湖南新式官立学堂有高等学堂、实业学堂、游学预备科、工艺学堂、中路学堂等12所”。在新式教育蔚然成风的形势下,士大夫出身的谭延闿顺应历史的潮流,积极参与到兴办新学的过程中,先后担任长沙中路师范学堂(公立)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明德学堂(私立)的校董等职务,并先后创办湖南第一女学堂、湖南中路公学、公立中等工业学堂等。
在兴学期间,谭延闿利用自己的名望和身份,对许多学堂校舍的修葺、教员的聘请和经费的筹措都不遗余力。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私立的明德学堂的资助和支持。明德学堂建立之初,由于是私立性质,尚无官方支持,经费紧张,于是他积极筹措经费,并以母亲李太夫人的名义,慷慨捐献黄金千两作为学校经费,而且承诺每年承担英文教员薪金一千元,挽救了尚处于襁褓之中的学堂。后来明德学堂的创办人胡元倓回忆道:“得谭君延闿助巨金”,学校始转危为安,因此,“请加入为创办人”,后来学堂毕业生纷纷留学归国,回校任教,在学校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其中的突出代表就是黄兴,这引起了顽固派的恐慌和攻击,“学校几至倾覆”,这时谭延闿为挽救学校出于水火,求援于巡抚赵尔馔,最后“得万金”,“该校生命,始有转机”,后来谭延闿又接任学堂的总理之职,“屡为借垫款,新增长沙校舍”,自此,“明德始议扩充”。
在谭延闿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湖南的新式教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至于谭延闿在兴办新式教育中的作用,在其年谱中有记载:“有关教育大计悉就公谘而后行,风气日开而莘莘学士翕然向风矣。”突出强调了谭延闿在兴办新式教育中的积极作用,虽然有拔高和溢美之嫌,但无疑却指明了谭延闿兴新学的不遗余力。
继“新政”破产之后,为了挽救处于风雨飘摇的统治,清政府于1906年又仿效外国,进行“预备立宪”。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不久,各地立宪派就积极活动起来,开始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湖南的立宪派也在1907年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推选谭延闿为主要负责人。
为了切实推进湖南的宪政以至全国的立宪运动,谭延闿等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对西方社会的了解,撰写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恳切陈词,切中要害,希望清政府组织民选议院,适时召开国会,并指出,只有召开民选议院,由议院立法,才能广开言路,才能真正实行预备立宪。况且这种民选议院还可以作为政府的监督部门,使国家的政令“不至大逆乎民志”。
针对清政府对实行预备立宪的犹豫与迟疑态度,谭延闿指出,实行预备立宪,中国“必须为君主国体,人民觉悟程度也渐趋增高,革命流血之事将可避免”。否则,就会“坐失事机,贻误大局,一旦革命爆发,则后果不堪设想,全局无法收拾”。这份请愿书震惊朝廷上下,或许是出于全国已经开展起来的如火如荼的立宪活动的压力,或者是出于对不立宪所产生后果的担忧,清政府于1907年颁布上谕,命在京都筹设资政院,“着各省督抚均在省设谘议局……并为资政院预备议员之阶”。继而在1908年又颁布了谘议局章程62条和议员选举章程115条。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湖南逐步展开了谘议局的筹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筹备工作,1909年8月6日,经过两轮的投票,选出了谭延闿等82名正式议员,这些议员于10月8日召开预备会议,大家一致公推谭延闿为湖南谘议局议长。
谭延闿当选为议长是众望所归,不仅是因为他是饱学的翰林、大清王朝的会元,而且因为他对新式教育、新式学堂的热衷,对湖南路权、矿权的争取和维护,对预备立宪的鼓动与支持,都为他赢得这一职位提供了群众基础。同时这一职位的获得,为谭延闿施展其政治抱负,展示其政治才华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一优势很快在接下来爆发的保路运动中显示出来。
鉴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攫取粤汉铁路的行为,谭延闿非常不满和愤怒,正因为此,1906年湖南铁路公司成立后,聘请他为谘议官,他欣然接受。
针对清政府要求粤汉铁路“官督商办”的要求,以谭延闿为代表的立宪人士,决定要在铁路“官督绅办”的基础上与清政府谈判,但无疾而终。后来,清政府为了继续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竟然在分享铁路利权的条件下,与德国、英国、法国等国签订粤汉铁路的借款条约。
湖南的保路运动进一步发展,此时谭延闿领导的湖南谘议局成为了运动的领导机关。谭延闿等议员不仅和邮传部、宪政编查馆等相关部门进行磋商和讨论,而且不断商讨募股集资的办法,为在与清政府的谈判争取有利的筹码。为了更好的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斗争,谭延闿等人创办了月刊湘路新志杂志,向人民解释集股拒债的道理,动员和鼓动人民为保护路权做出贡献。在湖南谘议局的具体安排下,在1909年8月开始修建长沙至株洲的铁路。1919年昭山至株洲的铁路也在湖南人民的努力下正式竣工,开始通车。
眼见人民的努力就要取得成功,清政府继而玩起“铁路国有”的把戏,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把粤汉等铁路收归国有。这种“国有”既是清政府厉行中央集权之策,又是其讨好外国,出卖利权之本。于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谭延闿为议长的湖南谘议局的领导下商讨应对之策。在谭延闿等立宪党人赴京力争仍无果之后,广大人民压抑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纷纷冲出学堂,涌上街头,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罢课风潮。但湖南当局却奉清政府的命令对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采取了高压政策,极力阻碍社会上已经暗自涌动的反清潮流。
湖南的保路运动是全国保路运动中发轫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虽然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声势大,影响深远,但无疑是全国争取路权的先锋。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党人,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担负领导与组织之责,表现相当活跃和积极,这表明谭延闿已经从一个封建制度的卫道士转变为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
争夺矿权的革命斗争,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官僚买办掠夺中国矿山的行径下刺激产生,它是20世纪群众性的收回利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利用谘议局议员的合法身份,对湖南地方当局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利权的卖国行径进行了多次斗争,不仅开会商讨应对之策,上书清廷据理辩驳,甚至谭延闿以辞去议长职位相要挟。然而清廷为了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拒不接受民意,毫无让步之意。这就加剧了立宪派党人和清廷的对立,谭延闿等人逐步走上了反清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