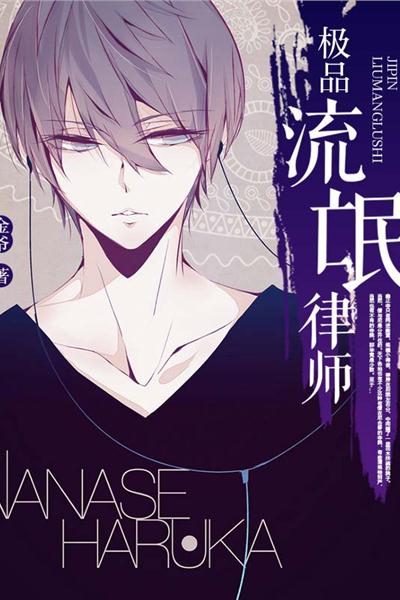“哈哈,开个玩笑,我们还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李治哈哈笑着,拍着李思文肩膀道,“头儿,你别在这耗着了,赶紧回家给大娘和思怡妹子报个喜讯吧!”
李思文沉吟道:“这不……还没到下班时间呢。”
李治佯恼道:“怎么,你还想赖在派出所啊?你已经不是派出所的人了,还想赖在这儿,你不挪位我们怎么上去啊?”
李思文忍不住笑了,李治这番话跟郑长顺可不一样,一个是开玩笑,是善意的,另一个却是满含怨愤的。
拍了拍手上的泥土,李思文叹道:“好好,那我赶紧走,免得你们恨我不挪位。”
说归说,李思文看着这班一起工作了几年的老下属,眼睛还是湿了。
所有人都在跟李思文挥手作别,只有郑长顺一个人心头不是滋味。
明明是他占了上风,到头来却落得如此凄凉的处境,而李思文却一步高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长顺没想到,这还是因为他并没有跟王治江等人同流合污,只是通风报信的事实在朱明宣等人的供认下,也是藏不住的。
好在这不算什么严重的违反纪律,要不然他就不是调到档案室那么简单了。
从派出所回家并不远,步行也就十分钟左右,李思文家就在鹰嘴镇北面。
鹰嘴镇的名称得于镇对面的一座山,山头凸出,弯弯的像一只老鹰的嘴,所以有了鹰嘴镇的名。
李思文排行老二,家里父母健在,父亲李广益在外做泥水工,母亲刘文春在家操持家务。家里有几亩田,喂了几头猪。姐姐李思琴嫁到另一个镇,也是农村,妹妹李思怡在县城一家餐厅打工,这段时间餐厅生意比较淡,员工轮周值,正好轮到她值班,因此不在家。李思文回家时,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在。
李思文出事并没跟家里人提起,加上他本身工作特殊,因此就算一连好多天不回家也是常事。
正经过镇上主街时,手机响了,李思文掏出手机来一看,来电显示是妹妹,赶紧接了:“小妹,怎么想着给老哥打电话了?今天回来吗?我回家给你和老妈做点儿好吃的……”
李思文心情不错,正想在街上买点儿菜回去做饭,不想手机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你是……李思怡的哥哥吧?我是她餐厅的同事,李思怡出……事了……”
“出事?出什么事?”李思文顿时紧张起来,停下了脚步问对方。
“今天中午,思怡负责的一桌客人酒喝多了,动手动脚的,要思怡陪他们喝酒,思怡不肯就被打了,脑袋被啤酒瓶砸破了,正在人民医院治疗……”
李思文一下子就急了,赶紧说道:“好,我马上到人民医院来,麻烦你帮忙照顾一下我妹妹。”
挂了电话,李思文心里又急又乱,也不买菜了,赶紧坐车赶往县城。
家里姐弟三人从小感情就好,姐姐李思琴比李思文大五岁,今年都三十出头了,李思怡比李思文小七岁,今年还才十九,从小就很黏他,李思文念中学时打了几回架,全是因为大孩子欺负妹妹。
到人民医院后,李思文又打通妹妹的手机,接电话的还是之前那个女孩,说已经住院了,在九楼十二病室。
电梯口站了几十个人,电梯升降的速度出奇的慢,李思文急得不行,直接从楼梯跑了上去。
一口气上到九楼,李思文气喘吁吁地找到十二病室,他稍微平复了下呼吸,这才推门进去。
病房里有三张床,最外边床上躺着一个人,输着液,一个女孩坐在床边盯着,另外两张床上没有人。
看到有人进来,那女孩抬头看过来,赶紧站起来问:“你是……思怡的哥哥?”
“我是!”李思文点点头,快步走到病床前,只见妹妹头上包着厚厚的纱布,脸上还有血迹,脸还肿着,都变样了。
李思文鼻中一酸,忍不住上前握住妹妹的手。
那女孩赶紧说:“医生缝了二十多针,打了药,说是镇痛的麻药,思怡睡了,还没醒,我……”
李思文见妹妹没有生命危险,当即镇定了下来,抬眼望着那女孩:“我妹妹的事店里怎么处理的?报警没有?”
女孩脸有些圆,脸上有几粒痘,听了李思文的话脸一扭,气愤地说:“报了,那几个客人好像有来头,这事只当小纠纷处理了,店老板说惹不得,算了。他只出五百块钱医药费,说全赖思怡不懂得敷衍客人,摸几下又不会掉块肉,让我送她来医院,交了两千块押金,思怡身上有七百,老板给了五百,我垫了八百……”
“谢谢你,一会儿我取钱给你。”李思文谢了那女孩,看看妹妹,心痛如绞,乖巧懂事的妹妹变成这样,他怎么不心疼。
“没事,就是替思怡生气。”那女孩摇摇头说,“思怡是个善良的女孩子,平时就我们两个最好,还邀我下周放假到你们家里去玩的,唉……”
李思文沉着脸,站起身来说:“麻烦你在这儿看着我妹妹,我出去一会儿,办点事就回来。”
那女孩点着头:“好的,没事的,老板说了让我照看着。”
李思文出了病房后狠狠地攥紧了拳头,妹妹被打成这个样子,他怎么也要替妹妹讨个说法!
妹妹上班的地方他知道,“长顺人家”,是县城比较高档的餐厅,只是他没去那儿吃过饭。
李思文先赶到餐厅,从店老板口中了解了详细经过后,眉头皱了起来,原来打他妹妹的人是牡丹园老板黄仕福的儿子黄少波。
这黄仕福是狮子县首富,通常首富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黄少波是个富二代,他老子辛苦挣钱,他则大把花钱。
面对这样一个大人物,连餐厅老板也劝李思文尽可能息事宁人,否则就是自找苦吃。
李思文当然不会就这么打退堂鼓,他决定找黄仕福一家讨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