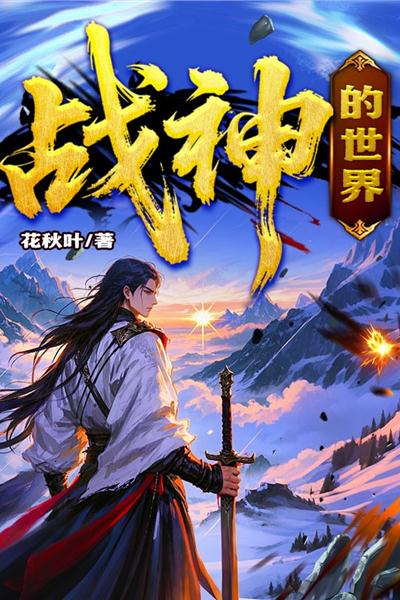周企若神色凝重,目若寒芒,功力渐渐催到了极限,身上衣衫猎猎荡起,回波涌动,静立在左侧靠培一张桌后,稳如山岳慕的!荤狼怪嚎一声,弹身而起,双劈握剑横剥宙出,剑化一道弧光,剑气纵横,奇快的斩向周企若的腰部!”
与此同时,血狼长啸一声,响切九霄,直层得屋宇不停摇晃,众人耳鼓嗡嗡雷鸣,身形候快,剑化寒星一点,疾刺向周芷若的咽喉。
二人心有默契,配合出手,威力无匹,封住了周芷若的所有退路周茫若芳心暗惊甫闻啸声,已觉强硕无匹的剑气排山例海船的卷至,冷一声:“找死!”呼的一脚踢翻身前的桌子,双腿一曲,奇快的自桌上疾滑而出,十指箕张,分抓二狼的丹田要穴。员劲疾掷而出。
“啊……!哼。”二狼出手快,周芷若比他们更快,剑招甫出,人影一晃即没,丹田被扣,痛入神镑,嘶心裂肺的惨呼一声,被一股强颈无匹的内气投起,凌空翻射而出。
怦怦两声暴响,撞破前面的门窗,飞弹向街心。
周芷若以快得不可思议的手法封住二人的真气,抛出室外,长长地格了摇头,走到地狼的尸体旁,暗运五层功力,平的一脚格其蹬飞向室外,拍手自言自语道:“这些无知之徒,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来找姑奶奶的麻烦,真是寿星翁上吊”活腻啦!”
栗子与婴子见周芒若举手投足间就将威震东瀛,不可一世的旷野七狼中的三狼打得死伤惨重,飞出店外不禁惊得目瞪口呆,良久始长长的吁了口气,跑到她身旁,一左一右的牵着她的手笑道:“夫人,你真神耶,功夫如此了得,在我们东派真是顶呱呱哟!”
二女说起汉语,语如连珠,清脆悦耳,娇笑盈盈,妩媚可笑。
周芷若不禁为之一悟,旋即拉着二女坐在桌旁嗅道:“好呀,你两个蹄子,原来会说汉语,竞当着我的面唁唁呱呱的说日语,是不是骂了我。”
栗子花容微变,旋即咱瞎笑道:“不敢耶,不敢耶,夫人昨夜一招间断了九州雄八人左管,武功高的可怕,我与婴于不敢亲近,伯不小心惹恼了你,你扭着我们的脖子咯咳一声,没命啦。”
婴子一旁娇笑道:“是耶,连那三个凶巴巴的男人都被你全扔皮球似的扔到了店外,我们弱不禁风,给你一扔,焉有命哉!”
二女一唱一合,周芷若忽然开心了不少,摇头一笑,灵智一闪,花容一闪,忽然想起了什么,花容微变道:“你们的何老板呢?到哪去了?我与那三个臭男人打斗了许久,并没有见他现身!”
二女大震,猛然想起了什么,疾道:“何老板去卧室着冷护法去了,极有可能听不到外面的打斗,他的卧室挺隐秘哩。”
周芷若暗松了口气,霍然起身道:“你们快带我去看看,如有意外,胜哥回来我可怎么向他交待哩。急死人啦,外面打翻了天,你们何老板不可能听不到半点响动。”
二女点了点头,起身牵着周芷若的手道:“夫人别急,婶子带你去。”语一出口,一左一右的牵着她疾朝后院走去,婴子边走边道:“夫人,你胜哥比你还厉害么,你似挺怕他耶。”
“我才不怕他耶。”周芷若玉颊一红道:“他的武功才是顶呱呱的,在中原武林,上天人地古往今来无人朗及,你们小小东瀛,自然更无其对手啦。”
“哇!这么凶啊。”二女不禁惊得呆大了双眼,栗子将信将疑的注视着周芷若边走边道:“夫人不会是大话唬人吧,以你的武功与他相比如何?”
周茫若见二女心有不信,摇头苦笑道:“没得比的,我胜哥练的是混合神功,我的峨蛆派武功与九阴百骨爪,只不过是其一身所学的九牛之一毛。”
二女长长的吁了口气。婴子若有所思道:“怪不得他敢单人匹马,独自一人前去救付总监等人,飞释道与奥羽堂的人遇见他可倒大屁啦。”
“倒大屁?”周芷若乍闻之下“噢咳”一笑,芳心暗惑,“汉文中可没有例大屁一说呀?”思绪疾转,恍然大悟:“是了,婴子乃是东瀛女子,虽在仁和客栈做事学不少汉文,却并非汉通,倒大霉的“雷”字一时想不起,才会说出“倒大屁”这种似是而非的怪话来。”
想通这一节,并不以为怪,与二女说说笑,走到后院,栗子一声不响的开了左侧浴室的门。周芷若芳暗异,“难道昨夜洗涣的地方就是何老板卧室。”
想起昨夜与耶聿长胜洗鸳鸯浴的那一幕,玉颊上不知不觉的泛起两朵红晕,缄口不言。栗子与耍子拉着周芷若走进浴室,从内反日了门,走到浴缸的左侧,在当中一块瓷砖上轻轻一旋,庞大的浴缸无声无息的移到门边,露出了一个仅容一人进入的洞口。周芷若一见之下明白了不少,心中暗叹:“原来这浴室内竞布有机关,怪不得婴于说何老板在卧室中听不到外面的打斗声,他的卧室竟是一个地下室。”
周芷若思忖问,栗子点了技蜡烛,猫身进入洞中,只得一声不响的跟在其身后,小心翼翼的朝洞内走去。
走下丈余地道斜转,变得平整了不少,游目四顾,但见四周全是瓷砖镶成,仅可容一人进出中暗票:“这何老板的小小客栈中竞有此设备,只怕他并非普通之人,说不准是那什么旅瀛安全会布在这一带的眼线。何况店中除他与两个婢女,就是厨子,火夫,及跑堂的,并不见其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