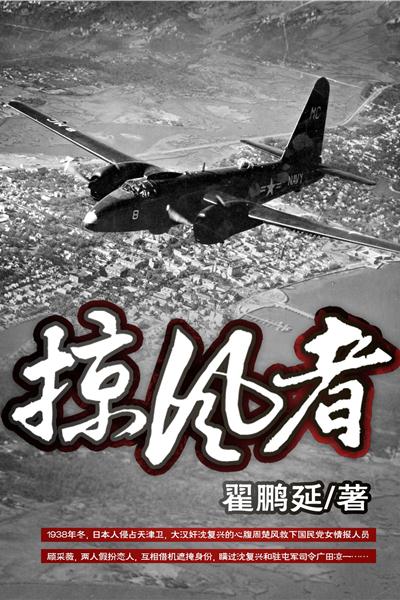已是深夜,秋雨连绵。后金都护副将府的机密室内,武长春正坐在灯下抄录词稿,打发这静寂的长夜。灯光映照着他那英武俊秀的脸庞,这是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又写得一笔柳体好字,在这微雨无月的深夜,笔端流出的是苏东坡那首《水调头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都护府的名称最早见著汉唐,当时,那是中央政府向西域地区派驻的管理机构。曾为明朝边将、建州卫都督佥事的女真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统一了白山黑水的女真各部,趁着明朝当局日渐衰落,自称为汗,叛明自立,准备取而代之。女真人的先祖曾经入主中原,建立金朝,所以打出了大金旗号,被人称作后金。明朝当局的谍报部门是锦衣卫,又称镇抚司,努尔哈赤为与明朝有别,便把谍报部门称为都护府。因这都护府完全是为了收集明朝当局的各种情报,所以除了都护府的最高长官指挥使为女真人——俗称满人外,多为投顺的汉人,武长春便是投顺的汉人。
武长春忽然停住,凝神细听,窗外隐隐传来骚动的声响和咕咕的叫声——那是鸽子的骚动与叫声。他立即搁笔,将窗推开,目光投向窗外的天井。那儿有棵盘根错节、叶儿凋零、歪歪斜斜的老槐树,树下树着个大鸽棚,一只飞来的公鸽正在一个有着一对鸽子的窝外,扇着翅膀扑啄窝窗,引得窝里的鸽子骚动不安,咕咕乱叫。武长春立即伸手在窗台上一撑,轻巧地跃过窗台,走近鸽棚,一把抓住那只鸽子,看着它脚腕缠着的绸带,好笑地想,这鸽儿刚从北京飞来,飞得也够远了,还要吃醋,准备与占了窝的情敌打架,劲头也够大的。他揭下绸带,取出一张纸条,又打开那扇窝窗,把手中那鸽子塞了进去,笑道:“这儿只有一个窝,一只母鸽子,你们谁有能耐就是谁的,鄙人严持中立。”说完转过身来,又是一跃,回到屋内,关上窗户,从抽屉里取出一只从俄罗斯商人那儿用一两金子买来、产自泰西的放大镜。他借助灯光与放大镜,看完纸条上那些微雕似的小字,心想:看来,这老秃子取代舒哈达的机会来了……
武长春是都护副将李永芳的书记官,李永芳是他的上司,也是丈人。李永芳原本为明朝驻守抚顺的游击,大前年后金大汗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胜明军后挥师南下,兵临抚顺。抚顺虽然城高壕深,粮草充足,易守难攻,但他没有抵抗,而是开门迎降,武长春也随着丈人一起归顺。因为李永芳是努尔哈赤起兵叛明、自立为汗后首个向他投诚的高级将领,因此对他大加犒赏,任命他为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都护使舒哈达的副手——都护副将,官位三品。对此,李永芳感恩不尽,因为工作努力而出色,颇受努尔哈赤与主管情报的四贝勒皇太极的赏识。昨天,李永芳就预感到这两天会有重要情报到达,要武长春晚上在机密房里当值候守,接到情报后随时报告。
于是,李长春便前往李永芳的卧室报告。然而,他还没走到门前,就听见卧室内传出女人兴奋的呻吟声。这种声音对他这样的年轻人尤其敏感,他马上明白,是那精力旺盛的老丈人正与那侍候他、刚过三十的老妈子激情交欢。李永芳是个鳏夫,其妻年初因病过世。武长春只能停在门口,耐心等到高潮过去,屋内变静,方才抬手敲了敲门:“阿爸……”
“是长春吗?”卧室内,正要入睡的李永芳从床帐里钻出脑袋问。虽说他还不满五十,身板硬朗,但早已谢顶,垂着一根勉强扎成的细辫子。
“正是。”
光着脊梁的李永芳赶紧把衣服套上,此时那个老妈子也把脑袋伸了出来。李永芳一见,朝她瞪了一眼,她又缩回帐内。
李永芳走到门口,把门打开,问着等在门口的武长春:“天亮的雨点儿回来了?”
“回来了。”
李永芳立即与武长春来到机密室,他推门走进后,没等坐下就问:“天亮怎么说的?”
武长春道:“天亮说,有迹象表明,胖子被锦衣卫盯上了,他已经通过一条暗道提醒过胖子,可胖子听不进。”
“这说明我们这儿很可能有内鬼!”
“阿爸怀疑是我们这儿的内鬼,向锦衣卫通报了我们在关内的细作网?”
“可能性很大,我早就提醒过舒哈达,但他听不进,还嚷着要把黄胖子派送北京。”
“那天亮会有危险吗?”
“不会,除了你,没人知道我把天亮派往北京,我连舒哈达也没说,你若不是我的女婿,我也不会告诉你,搞情报的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要是舒哈达知道,阿爸背着他重新埋下一条暗线,准会恼羞成怒,这小子从来就瞧不起咱们汉人。”
“怕什么,我这样做是四贝勒批的。四贝勒清楚,舒哈达能力有限,对我又不满与猜忌,不肯放手让我行动。以前他不把舒哈达换掉,主要是他的家族都曾支持过四贝勒。如今,四贝勒接班早已铁板钉钉,只是碍着过去的情面才没把他换掉,有些事,他都是暗中与我商量,征求我的看法。”
“真没想到,四贝勒这么信任阿爸。”武长春意外地感叹道。
“四贝勒不但雄才大略,而且知人善任,满人中,唯有他才清楚,没有汉人,想要入主中原一统江山,那是做梦,咱们靠上这大码头错不了。”李永芳说时既佩服又自信。
“这个消息是不是马上向他报告?”
“不忙,当下谁也救不了胖子,等天亮送来报丧的帖子再报告也不晚,你快去睡吧。”
李永芳刚要离开,又想起似的,“长春……
“阿爸还有什么事要交待?”
“你结婚也四五年了,还没儿子。你该明白,生儿子的事,也不能单靠秀琴,你也要努力啊!”
“明白了。”武长春一想到那一身赘肉、毫无柔情又无感情的老婆,就会丧失努力的欲望。
往年,北京的秋天总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然而今年——也就是大明天启三年的中秋刚过,不到傍晚,灰蒙蒙的雾霾就笼罩了北京城,到了夜晚即有混沌一片的感觉。然而城内灯多,特别是八大胡同的胭脂胡同,门庭之间灯火相连,更是辉煌。那儿的雾霾被染得黄晕,亮得怪异,空中还飘浮着隐约、缠绵、丝竹与牙板伴奏的女子歌声。八大胡同中有七条是直的,也不长,唯独那深长的胭脂胡同不能直走到底。八大胡同是买春的地方,妓院众多,但那高级妓院都设在这曲里拐弯的胭脂胡同里。客人们一进这条胡同,就有一种曲径通幽的微妙感觉。这儿的姑娘净是百里挑一、从江南水乡精选而来,几位挂头牌的姑娘,不但长得俏,还能吹拉弹唱,擅长诗书琴画,绝对是色艺双全。不过,这儿的花销也不低,往往是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所以前来娱乐的客人,都是些达官贵人与挥金如土的豪富。
笃!笃!笃!笃!笃!笃!……
初更的梆子声在胭脂胡同内响起,一个游魂似的巡夜更夫用那昏睡般的声音喊道:“注意灯火!关好门窗!防火防盗!平安过夜!”
更夫的梆子声和叫声渐行渐远,身影也随之消失,不久,又一个身影出现在胡同里。此人身着便装,浓眉大眼,肩宽膀圆,腿长腰细,是那种经典的健美型的身材,但他没有胡子,低首欠身,匆匆行进,生怕别人见着似的。因为雾霾和低头欠身,没能注意前方,突然被迎面而来、摇摇晃晃的一个身影撞了一下。他抬头一看,是两个年轻的醉汉,他也不想与他们论理,想要绕过他们继续前行,可那撞他的年轻人却一把将他当胸揪住,骂道:“妈的,你眼睛瞎了?”
年轻人正要发作,挥拳撒野时,另一年轻人震惊地叫道:“马公公?”
想要撒野的年轻人,是北京菜市口最大的肉铺老板的儿子常贵,他也认出了被他“瞎了眼”抓着的是宫中的太监马楠。以前,马楠当过司膳太监,常去他家进肉。他唬得酒也醒了,赶忙松手,先朝自己的脸上扇了个巴掌,扑跪下来:“小的该死,瞎了眼的是小的,小的马尿喝多了,有眼不识公公……”
“滚!”马楠不想与他纠缠。
常贵一听,反应极快地就地一滚,让到一旁,等马楠过去,方才支撑着爬起,疑惑地朝他背影看着。前方的身影刚一消失,常贵便好笑地道:“张琪,你说一个下面没了的太监,来这儿干吗?”
“也许他有自个儿的玩法。”
“不可能!宝贝没了,肯定没有玩兴!”常贵这样联想,说得那么肯定,是因为今天下午,他和几个小兄弟在小梨园里玩到现在。小梨园也不算低档,在胭脂巷里算是大众型的,不但价格相对便宜,而且经常打折优惠。这小子没说错,马楠是个太监,太监没有这种需要,要是没事,他才不会来这儿呢。因为,一个没了宝贝的太监,独自钻进胭脂胡同,肯定会成为北京城内的热点新闻。还有,这种地方会让他感到屈辱和伤心。
马楠以前也是一条硬朗的汉子,曾给马帮和镖局当过马夫,他没想到,十八岁那年,两匹没有阉过的种马,为了争夺一匹母马踢斗起来,他想把它们分开时,不幸被乱踢的种马踢碎了睾丸,当场昏死过去,后来虽被救活,可是完全丧失了男人的功能。为此,他曾痛不欲生,想去寻死,但他最终没去,而是想,既然事情发生了,不能为家人传宗接代,那就干脆自宫,去当太监。碎了睾丸的人,自宫时没啥痛苦,风险也不大,这也是一种致富的捷径。他是河北保定人,太监是那儿的特产,他见有些太监入宫后,很快就暴富起来,为自家的亲人在老家置房购地,让人羡慕。他儿时曾进过两年私塾,太监中识字的不多,他有当个好太监的优势。没想到进宫后,这儿的生存环境比外界还要复杂,他好不容易弄到了司膳的位子,干了不到三年,就被魏忠贤的一个远亲夺了,把他调到秉书房里当司笔太监。这是升官不发财,因为司膳太监掌管着皇上与他眷属的伙食,油水特足,地道肥缺,而那司笔太监只有一点可怜的干薪。马楠认为,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人生有三大追求:女人、权力、金钱。现在他对女人完全失去了兴趣,剩下的只是权力与金钱,然而权力离他远着呢,近在眼前的只有金钱。今天,他就是为了钱,趁着黑夜,钻进这雾霾笼罩的胭脂胡同。
马楠在胡同深处一个庭院的门前停住,门前的灯笼不算太大,正中写着“小白楼”三个字,没有挂牌姑娘的名字,不像其他庭院,门前的灯笼上都有挂牌姑娘的艺名。这说明院里的姑娘都被高价包养了,用不着挂牌。马楠没敲门,而是倾耳细听,当他听到隐隐传出的“高山流水”的古琴声,知道门没上闩,方才轻轻地推门进院,把门关上。这是他上次做完买卖后,特为关照小白楼的头牌姑娘玉玲儿,下次再来,客人到了,门没上闩就用“高山流水”来暗示他,他不愿意敲门,以免惊动别人,为此,还给了玉玲儿五十两银子的谢金。
小白楼的院子挺大,花木扶疏,池水清澈。马楠进院后,沿着一条青石铺就的甬道朝着前方的小楼走去。那是一幢江南常见、北京少见、粉墙黛瓦的两层小楼,故称小白楼。小楼内的厅屋挺宽敞的,布置得也相当雅致,墙上挂着的字画都是出自名家之手。正墙上挂着的那幅充满灵气、颇具意境的字“曲径通幽小洞天”,就是明代才子徐铭贞到此一游留下的手迹。厅屋西边有一张琴桌,桌前的小香炉里飘着袅袅青烟。清秀文静的玉玲儿正坐在琴桌前弹奏着古琴。
吱呀一声,门被缓缓推开,马楠跨过门槛:“玲姑娘。”
玉玲儿抬眼一看,浅浅一笑,收住手,款款起身:“马先生……”
这也是马楠关照的,到了这儿,一定要称他先生,别叫公公。公公是太监的称呼,说不清是尊是贬。马楠随手把门关上:“黄先生可来了?”
“早来了,上面等着呢!”
“那我过会儿再来欣赏姑娘的小曲。”说着,马楠径直朝楼上走去,来到楼上那透出灯光的包房。他把门推开,进门一看,疑窦顿生。这套包房有前后两间,前间是客厅,后间是卧室,眼前的客厅空着,吊着的宫灯却亮着。
“这小子大概下午就到了,一来就与他包养的姑娘玩了起来,肯定是玩过火了,累趴在床上,还没醒呢!”马楠冷笑着想。他又干咳几声还不见动静,忍不住地唤了起来:“黄先生!”
然而,随着走动的脚步声,马楠脸上闪出震惊的神色。
一个身着金飞鱼服的人影背着手踱着方步,悠然地走出卧室。金飞鱼服是锦衣卫特有的制服,这是锦衣卫的侦探头目佥事田尔耕。此人长得相貌堂堂,精干结实,有一双黑而发亮、透着冷光的眼睛,是个武举出身、功夫不浅的官僚。田尔耕见马楠呆在那儿,故作惊诧地:“哟!是马公公?没想到,咱们竟能在这青楼里幸会。”
马楠自控的能力极强,马上稳住自己,挤出笑脸:“这不是锦衣卫的田大人吗?”
田尔耕微笑着:“马公公的记性真好,咱们只是在前年祭天大典时见过一面,您就能记住我。”
“田大人这么帅气,谁见了都不会忘记。”马楠的话音刚落,身后传来关门声,他回头一看,门前出现四个毫无表情、身着短装的彪形大汉。
田尔耕走到桌前,拿起桌上的茶壶,沏了杯茶,推到对面,又给自己沏了一杯,把手朝对面座位一伸:“坐,马公公请坐。”
马楠只得在对面坐下,看着跟着坐下的田尔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