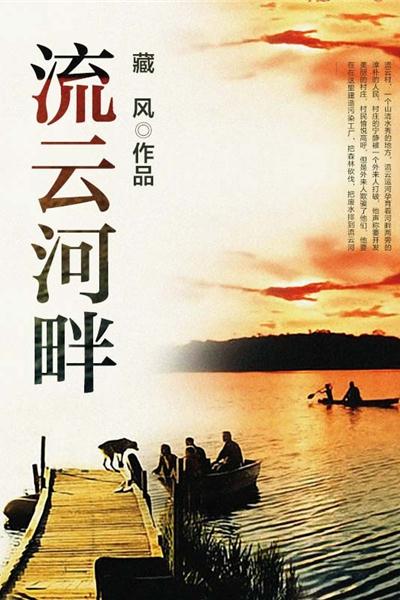1951年夏天,小狐狸事件两个月后,我和二姐一块儿被父亲送到靠屯街读书了。
靠屯街是一个小镇,离牛家坨子四里多地儿,镇上有医院有商店有学校有集市……这对住在坨子的屯人来说,无疑是个大都市了。屯里人去一趟靠屯街,很当一回事儿,除了几个月或几天不洗的脸,要洗一遍外,就连说话的声音都不一样了,这个问,干啥(gaha)去?那个答,答时往往小脖儿一挺,声音提得高高的:上街(gai)去。街,指的就是靠屯街。
此前,我大哥大姐都在靠屯街读书了,现在,也轮到我上街了,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父亲读过三年半书,在农村也算一个文化人儿,他的儿子们还没出生,他便想好了儿子们的名字,无非是套用儒家经髓“仁、义、礼、智、信”几个字儿,希望他的儿子们,能守护好做人的本份。也是上天佑他,他选了这五个字儿,上天给了他五个儿子。我是老二,责无旁贷地担起了“守义”这个名字。
上学是件好事儿,对学校一切都是新鲜的,但对自小在荒野里跑惯了的孩子来说,三天新鲜劲儿一过,脑子里牵挂的,还是我家的大河套。
敢把大河套叫成我家的,那里,确实和我家因缘匪浅。
前面讲过,伊通河经常发大水,沿河两岸,人们修了长长的防水壕。壕内,是屯子和田地,壕外,便是大河套了。大河套里生满了灌木蒿草,也成了动物们的乐园,尤其是狼,每天晚上都会传来它们长长的嚎叫声,如此,也让河套成了屯子里的禁地。
父亲来到牛家坨子后,分了田地,但他不安分的性格,又盯上了大河套。他看上了大河套这片荒野,还有荒野中流淌的那条大河。父亲在屯人嘲笑的眼光中,带着老婆孩子,在荒野中开出十几亩田地,还在地边儿盖了一座泥土房,为他的下一步计划,埋下了伏笔。
父亲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向伊通河进军。
当时的伊通河,很宽也很深,大清对沙俄的雅克萨之战,运粮船走的就是这条水道。伊通河自北向南流来,经过父亲盖的房前,来个急转弯儿,向东流去。河流拐湾处,留下一个大泬水崴子,当地人叫回龙崴子。回龙崴子的水很深,也是鱼虾聚堆儿的地方。父亲贩鱼时,知道捕鱼的道道儿,他和母亲用了半冬时间,织出一片大扳罾网。扳罾网织好后,杀头猪,将网用猪血浸泡好,如此,渔网像上了层胶一样,不但不烂,还和河底一个色儿,引不起鱼虾怀疑。有了网,再砍出网杆子网架子,开春时,求人帮着将网下到了回龙崴子里。
发明扳罾网的人,绝对是个天才,也一定是个懒人。只在河里下片网,不时拉出来看看,就把鱼儿从水里捞出来了。扳罾网的网片很大,二十多平方,边上的网眼大,越往中间越小,到了正中间,连个小泥鳅也跑不出去。起网时,网从四周拉动,鱼往中间奔,奔到中间时,四周的网,早已提上水面,便无处可逃了。挑起这片大网的,是一个十五米长的大杆子,杆子头,挂着一个大十字架,十字架的四端,拴上网的四个角。同时,在距岸边两米远的水中,埋上两根立柱,立柱高出水面两米,立柱上放一个横梁,主体网杆就放在横梁上。主体网杆上端拴一个梯形绳,放开梯形绳,主体网杆通过十字架,便将网插进了水底。起网时,拉动梯形绳,主体网杆就会把网片撅出水面,鱼就被集中在网兜中了。此时,人踩着横梁上的木板,近前用长杆抄罗子将鱼舀上来,再将网放进水底。
网太大,被水拉着,没有点力气是拉不出来的。起鱼的活儿,成了父亲的专利。
我经常和大姐、大哥、二姐、三弟看父亲扳鱼。那是一种期待与猜测,就像听故事,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结局一样。起网的结局,就是想看到都网住了一些什么鱼儿?扳罾网,虽然守株待兔,效果却非常好,尤其到了汛期,汹涌的水流,让整条河的鱼儿,都兴奋得活动起来,它们游到回龙崴子,水流减缓,鱼儿停下来小憩,如此,就到了父亲丰收的时候。
父亲贩鱼时,结识很多鱼贩子,晚上打上来的鱼,一清早,全被鱼贩子挑到各屯叫卖去了。
父亲专事打鱼,母亲则忙活着田地的活儿。大河套的地,除了主要作物高粱,母亲又在上面种上了各种瓜果蔬菜和花木,看上去,就像一个大花园儿。
整个暑假,我们家这些孩子没事儿可干,母亲也怕我们和屯里孩子打架,将我们全集中到了大河套里。
此时,我家已有了七个孩子,七个孩子三男四女,按性别组成了两伙儿,姑娘在大姐带领下,玩着女孩子的东西,欻嘎拉哈(猪或羊的膝骨,欻,象声词,源自满语,声音动作全兼)呀染红指甲呀……小子们,大哥则成了头儿。大哥守仁这一年上小学三年级,他驼背,不爱说话,但很聪明,河套里跑的野鸭呀野鸡呀獾子呀兔子呀……他都有办法捉到。如此,大哥便成了我们这些小子当之无愧的领袖。
每一天,大哥带我们出去时,母亲总不忘嘱咐一句:“不要走远了,小心狼。”
东河套里,狼确实多,尤其我家搬来后,父亲在河套里又养了猪和鸡,猪鸡的叫声,成了狼的诱饵。黄昏时,空寂的河套中,经常能听到狼的叫声。为了防狼,我父亲买了一杆老洋炮(土枪),每到晚上都放上一枪,空荡的大河套,将枪声传得很远很远。母亲为了保险,每到傍晚,让我们再在房前点上一堆火,压上青蒿子,浓浓的带有艾香的草烟,既驱赶了蚊子,也将人的气息散发了出去。
父母的这些防犯措施很管用,就连牛家坨子猪鸡都常被狼叼走,我们置身在荒僻的大河套里,生活在狼的地盘上,养的猪和鸡,却没损失过。
这样的日子,我父亲很喜欢,多年后,回忆起那段生活,他脸上总会溢出一层神圣的光来,带着回忆的口气说:“建国那会儿,老百姓过的那才叫好日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