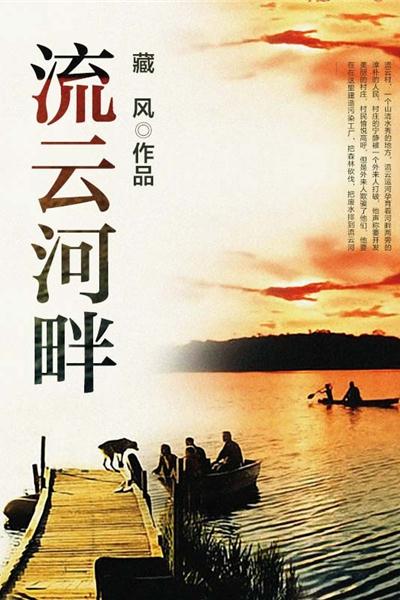时间晃悠到了1957年,这年夏天,我和我的几个好朋友,一同考进了农安县第六中学——靠山中学。
整个小学阶段,我们这一帮好得不能再好的朋友,可惜上了中学,却被拆开了。牛淑芬和张中原分在一班,牛淑芬当班长,张中原当学习委员;我和谭斌钟玉花分到二班,小学时我梦想当班长,这回美梦成真,真的当上了班长。牛家坨子我那些亲属,只有我一个人考取了中学。
听说我考取了中学,还当了班长,父亲母亲和我一样高兴,特别是父亲,阴沉了几年的脸,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三年前,某人一篇文章——《谁说鸡毛XXXX》(此处略去620字)……中国的这场风暴,刮到我父亲头上,是刮走了土改时分给他的田地和他在大河套开的田地,还有扳罾网和渔船,让他成了生产队的一名饲养员,给队里喂猪。
我父亲本来不爱笑,这回,脸上更没笑模样了。
社会上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我家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姐结婚后,没有再读书,她富裕婆家的窑场,也成了XX窑场,大姐同大姐夫不愿入队,去了辽源煤矿。大姐夫在煤矿下井,大姐学会了理发,开了一家理发馆儿。二姐有人给介绍了对像,是黑龙江银春林区的一名伐木工人。二姐夫老家也是牛家坨子的,几年前随他大哥去了银春,在那里开运材拖拉机。二姐的婚礼,是去林区办的。临行时,父亲派大哥当代表,送二姐去林区成婚。大哥两年前就不上学了,入了生产队。大哥送二姐去了林区后,卖一个搭一个,也不回来了,在那里当了一名汽修工人。
牛家坨子这几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分出四个生产队,所有能干活的人,都成了XXXX社员。“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就是藤上的瓜”,但是,很多瓜不愿意拴在藤上,有点门路的青年人,能走能逃的,都走都逃了。表哥佟万贵,带着弟弟佟万清去了银春;表弟佟万祥,去了内蒙古;表姐佟玉华,结婚后和丈夫去了哈尔滨……最让我没想不到的是,表弟佟万清从银春干了半年回来,求我母亲当介绍人,竟然和串铃子结了婚。婚后,王麻子带着一家老小,也跟着去了银春。
牛家坨子,往外走了很多人,也死了不少人,我外婆和外公,也都在这两三年间相继辞世了。
对于社会上的变化,最不适应的是我父亲,他十万个不愿意,又不得不到生产队里去喂猪。如果不入队,连口粮都买不到,全家人只能饿死。
父亲在生产队里喂猪,不知为什么,竟和生产队长陈大肚皮结了梁子。
陈大肚皮绰号的由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胃王。解放前,陈发最喜欢的活儿就是给地主扛活,扛活地主家供饭能让他吃饱肚子,但一段时间后,一些小地主听说来找活儿的叫陈发,无不以各种借口将他打发了……地主如此,就是他太能吃了。有个小地主不相信还能吃穷,准备了一升面(五斤左右)的馒头,还有一个大猪头,想看看陈发到底能吃多少?陈发在众人注视下,将一升面的馒头和一只5斤左右的猪头全吃了下去……小地主当时就被吃哭了,道:“你是爷,我收回我说的话。”
陈发因为吃不饱饭对旧社会苦大仇深,土改控诉时,他和他父亲轮番上台,控诉的内容都是关于吃的,就是地主太狠,不给饱饭吃……但是,土改后他家分了房子分了地,还是吃不饱饭,我家成了他家的主要借粮户。按屯邻亲论,陈发管我妈叫二姑,管我爸叫二姑父,那时的陈发,每每看到我父母,二姑二姑父的叫得满天阳光,自从成立了XX公社,陈发当上了牛家坨子十七小队队长,从此不用再借粮了,也不愁吃不饱饭了,脸色一下变了,对我父亲也不叫二姑父了,高兴时喊老张头,不高兴时就喊张海怪。我父亲本来就不同意入社,入社后,看见陈队长每天的工作就是琢磨吃的,将生产队那点家底儿恨不得全装进他一个人的肚子里去,心里就更加不痛快了,尤其是陈发还改了称呼,让他的自尊心更是受了打击,我父亲恨得直咬牙,背后骂他攮屎包、非益畜。
父亲在队里受到陈发欺负,心里从来没服过,用他的话说,掐半拉眼珠子也看不上老陈家的人。“老陈家的人”指的是牛家坨子整个陈氏家族。不过也有例外,陈氏家族的人,也有一个让我父亲喜欢的人,叫陈长荣,绰号陈哈哈。陈哈哈比我大几岁,在县里一所会计学校毕业后,放弃城里诱惑,回牛家坨子当了一名农民。陈哈哈回牛家坨子,是奔一个绰号小骚狐狸的女人回来的。小骚狐狸叫田美英,是个标准的美人坯子,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而且还会美,从少女时代起,也不知她家怎么就能擦得起雪花膏,小脸儿总是擦得白白的,一白遮百丑,再配上她那双桃花眼,哪个男人看了,没有不骨软筋酥的。
据说,陈哈哈上小高时,就和小骚狐狸那个了,因此,在别人都在纷纷逃离农村时,他却一反常态,不顾家人反对,拼命回到屯子,和小骚狐狸结成连理,在生产队里当了一名会计。
父亲说,一个男人被女人牵着走,这辈子都没出息。父亲如此说,还是很敬佩陈哈哈的才气,家里有什么事儿,他不请队长陈发,却请会计陈哈哈。
人民公社的愿意被现实生活击得支离破碎,作为最底层的社员,父亲只有六个字——一切都看不惯。他看不惯干活大帮哄,看不惯社员随意浪费财产,看不惯社员对生产队的一切不管不问,看不惯社员每天抬个脑袋,就知道朝生产队要粮吃……其中,最看不惯的还是那些满嘴漂亮话、一到下边就穷吃脏喝的干部。上面对公社大队生产队抓得很紧,三天两头,就派人下来检查,一检查,生产队就要杀猪招待……看着自己亲手喂大的猪一头又一头被抓走,父亲心里不平,没事儿拿个猪食瓢敲打着猪槽子,用骂猪来发泄心里的恨意:你们这帮造粪货,我他妈天天喂着你们,你们除了造粪瞎哼哼还能干点什么?父亲的三七话,让陈发知道了,如此,父亲就更不得烟抽了,有事没事儿,陈发总找父亲的茬儿。父亲心里积了很大一股火,一天,陈发又带人来猪场抓猪,父亲猪食瓢一扔,当场将陈发痛骂一顿,又公社将陈发告了。
陈发的罪名无非是大吃大喝、贪占集体财产、搞破鞋。
上边派人来牛家坨子调查,陈发陪同调查人员继续杀猪,继续大吃大喝,两天后,没抓陈发,反而将我父亲抓走了。
父亲的罪名是诬告罪和破坏生产罪。
诬告罪:多吃多占,会计那没记录;搞破鞋,没有娘们儿承认;破坏生产罪,却是有据可查——生产队死过一头老母猪,说是我父亲打死的。
父亲被抓后,全家都急坏了,妈妈更是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有人给出主意,要想让我父亲早点出来,非找陈哈哈不可。
我和母亲去求陈哈哈,他一口答应,然后说:“我可以去找陈发队长,让他放了二姑父,不过,一定不要让二姑父再告了。队长多吃点、多喝点、多拿点,这在哪个队都是正常的。你说他搞破鞋,那是老娘们愿意被搞,与别人有什么关系?”
陈哈哈的话,听着不对味儿,但有求于人,我也只能千保证万保证,说父亲出来,再也不告了。
父亲被关了三天,给放了出来。
陈哈哈找陈发怎么说的不得而知,但是有一天,陈发突然问我:“你是有两个大伯当胡子吗?”我说不知道。想来,一定是陈哈哈以此要挟过陈发,话也可能是这样讲的:你就不要和张海怪闹了,闹大了对谁都不好。张海怪两个哥哥,都是当胡子的。现在是没胡子了,保不准儿,那哥俩在哪猫着呢,他们杀个人,和你杀头猪有啥区别?再者说了,咱牛家坨子,谁敢去东大河套开荒种地打鱼?这样的主儿,你要逼急了,他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父亲出来后,在家里摆了一桌酒,请了陈发和陈哈哈,一斤白酒,消除了两家的梁子。
这件事以后,陈大肚皮见了我父亲,又改称二姑父了。我父亲虽然还是看不惯,但每天还是不得提着猪食瓢,到生产队去“咯唠”“咯唠”叫猪喂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