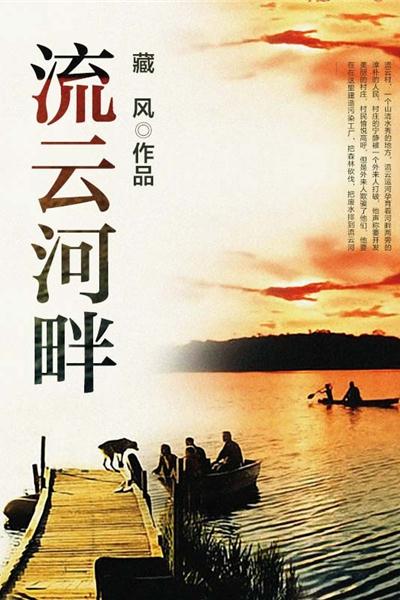1960年的春节到了,一大早,在冻僵了的东北煤城,开始有了零星的鞭炮声,尽管是大饥饿年代,大家并没忘记这天是过年的日子。
教师培训班,就剩下了我和老夫子陈嘉良以及山东秀才鲁余粮,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打伙过这个冷清的春节了。
昨天傍晚,表姐领着大宝来到了培训班,表姐说,无论如何要去她家过年。表姐的情意我领了,但我告诉表姐,我这里还有两个朋友,我不能丢下他们,最后,我答应初一去她家。表姐刚走,郑老师又来了。郑老师让我们几个去她家过春节,但被我们拒绝了。我们三个大男人,怎好去打扰刚离婚的老师呢。我们刚拒绝完郑老师的好意,耿科长随脚又到了,她看到培训班就剩下了我们三个人,让郑老师打个报告,她在科里给我们争取三份春节物资分配名额。老夫子领回来时,我们看到是每人半斤油、一斤酒、二斤肉、二斤鱼、二斤大米、二斤白面……在人人饥啼号寒的的年代,国库里还能存下这些好东西,我们连想都没敢去想。
我们三个人轮番捅着火炉,炉盖子烧得红红的,寝室里温暖如春。我们没有写春联,也没有放鞭炮,除了没有那份闲情逸致,更没有那笔闲钱,大家的心思都集中在肚子里了。
鱼和肉都是冻的,冻得比冰坨子还硬,我们把它们放到一个大水盆里,用凉水缓上。自从鱼和肉放到水盆里,老夫子就蹲在盆子边儿,不错眼珠地看着,不时用棍子捅一捅,不时涌上口腔里的酸水更引发了他的酸劲儿,他摇头晃脑,大有孔乙已的风范:“不多也……唉……多乎哉!不多也!”
鲁余粮奚落他:“老夫子,你不要管多乎哉了还是不多哉,还是赶快下厨房吧。”
老夫子不情愿地说:“多乎哉是咱们三个人共同多乎哉,为什么就得是我下厨?你的陈山月同学不是也来么?让她做菜好了。”
鲁余粮说:“陈山月来不来我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她告诉你了?”
老夫子脑袋晃得像个拨浪鼓,气哼哼地说:“好你个秀才,你到是挺会装。你敢说她一会儿不来?她要是不来,我把陈嘉良的‘陈’字倒着写。”他停了停,还没有发泄够,枪口又对准了我:“还有你张守义,谢玲回家了,不然她会离开你一步么?你们俩真是春风得意啊,艳福不浅也。”老夫子“也”字拉得长长的,里面包含了羡慕和嫉妒。
我说道:“老夫子,请不要扩大打击面好么?我和谢玲又没招惹你。”
老夫子摇摇头叹口气:“你和谢玲是没招我惹我,秀才和陈山月也没招我惹我,你们谁还有闲心招惹我呀?我只是不平衡。你们成双成对,形影不离,我老夫子真就那么差劲么?凄凄惨惨戚戚,形单影只,孤家寡人,身饿心饿瞎逼逼……唉,真是天道不公也!”
就在老夫子哀叹时,寝室门被推开了,陈山月和倪春萍裹着寒风走了进来。她俩的到来,如同两道靓丽的风景线,霎时间让昏暗的寝室有了光彩。她俩都换上了节日的新衣服,着意画了妆,显得非常清新、秀气。
陈山月小脸冻得红红的,摘下红红的围巾笑着问:“方才谁说天道不公了?天道怎么不公了?我们找他问问去。”
我和鲁余粮被陈山月逗得大笑。
老夫子以为陈山月她们听到了他的抱怨,非常尴尬,连脖子都红了,正不知所云时,山东秀才替他打了圆场。鲁余粮说:“是老夫子说天道不公了。他因为你们只顾自己在家过年,抛下我们哥们不管,这不抱怨你们不够哥们意思呢吗。”
山东秀才的话让她俩信以为真,倪春萍居高临下的道:“还天道不公呢,我们可是抛下家里人来看你们来了。”
我油腔滑调地说:“谢谢,谢谢两位小姐的隆情厚意,在下十二分感谢。”说完这句话,我感觉有些不着调,她们毕竟是来看我们的,我赶紧拿出糖果捧到她们面前,真诚地说:“请吃糖”倪春萍露出喜色,抓起一把糖递给陈山月,说:“山月,吃糖,我们不就是来吃糖的么。”
鲁余粮说:“拜托两位,麻烦给老夫子打打下手,我们的肚子早就咕咕叫了。”
陈山月说:“就你的肚子爱咕咕叫,你们山东产的八百斤一个的大地瓜,还没把它填满啊。”
当时XX日报上说,山东某社,在XXX思想指导下,科学种田,地瓜长到八百斤一个。同学们读到报纸,嘲笑鲁余粮,都要和他去山东吃地瓜。
鲁余粮听陈山月又提到这事儿,生气地说:“那些二逼报纸发的东西你们也信?我们家乡不要说有能长八百斤一个的大地瓜,哪怕就是有地瓜秧吃,老百姓也不会颠沛流离都去逃难了。”
老夫子说完这句话,气呼呼端起鱼肉去了厨房。
陈山月对我一伸舌头,拉着倪春萍跟了进去。
我往炉子里添了两铲煤,也去了厨房。看到他们又说又笑忙活着,我心里十分高兴,对老夫子道:“拜托你好好施展一下手艺,我插不上手,回寝室烧炉子吧。我把炉子烧得旺旺的,好等着品尝你的拿手菜。”
老夫子笑着说:“你小子就懒吧,要把屋子烧不暖和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回到寝室,想到他们在冰冷的水盆里刮鱼鳞,就觉得好笑。倪春萍能在大年三十来看我们,绝非偶然。她不可能是来看我和山东秀才的,那就是老夫子了,从她看老夫子的眼神,我已经看出了端倪。人真是个奇怪动物,倪春萍虽算不上漂亮,却也不算难看,毕竟是二十几岁的大姑娘,青春造就了每一个女人的美丽。倪春萍能看上又酸又臭的老夫子,也算老天爷对老夫子的眷顾了,但愿这是真的。我想起摸底调查时,谢玲奚落倪春萍的话——真是慧眼识英雄啊。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有人敲门。我以为陈山月或倪春萍在故弄玄虚,大声说:“愿意进来就进来,别把门敲坏了。”随着我的话,门推开了,一股浓烈的脂粉味儿夹裹着寒风扑鼻而来,抬眼一看,毫不夸张地说,我当时真是惊呆了,竟然是糊涂美人浓妆艳抹走了进来。糊涂美人把过年的喜兴全穿身上了,一件十分显眼的红花棉袄,一条鲜艳的绿围巾,一条黑色的大绒裤子,给人的感觉,就像寒冬里绽放的一朵大土豆花,而这朵大土豆花的花粉又特别多。当糊涂美人拿掉围巾时,将她的糊涂化妆术再次暴露无疑。她的小脸上涂了层厚厚的脂粉,脸蛋和嘴唇都涂得红红的,其余部位都白白的,脖子依然黑黑的,不同凡响的是,糊涂美人这回把眼线和眉毛也涂得黑黑的,就像马上要登台演出一样。
糊涂美人放下挎包,抬眼在寝室看了看,问我:“张守义,怎么就你自己,陈嘉良和鲁余粮上哪了?”
我开玩笑说:“我一个人还不够夫人享用么?”
说完这句话我就后悔了,以前我们也开玩笑,可从来没有太过份。我观察她的反应,过厚的脂粉无法看到她的脸是红是白?就在我揣摩她的心思时,她却说出了让我更震惊的话:“你小子都饿得前腔塌后背了,我就是想享用,恐怕你也没那本事了。”
糊涂美人直白得让我害怕,她的眼神更让我害怕,我不敢接她的话茬,顾左右而言他,道:“不和你开玩笑了。老夫子和鲁余粮在厨房忙活呢。陈山月和倪春萍也来了,他们在做菜。你去看看,露两手给他们看看。”
糊涂美人不屑地道:“我没兴趣去看他们。年三十了,我是特意来看看你这个有家不归的人,顺便拿点东西慰劳慰劳你。”
她打开挎包,从里面拿出两包用草纸包裹着的东西和两瓶酒,说道:“张守义,这是姐姐一点心意,祝你春节愉快。”
还没等我搭腔,糊涂美人急匆匆地走了。
糊涂美人带走了她浓烈的脂粉香,却给我留下了一阵不安。我不相信她会来看我,可她不看我又看谁呢?管它呢,还是看看她到底拿的什么东西吧。我打开纸包,一包是切好的肘子肉,一包是一个还流着油的香喷喷烧鸡。
看到这两样东西,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响,已经和肉绝缘的脑细胞突然惊醒过来。此时,已经顾不得别的了,拿起两片肘子肉就放进了嘴里,这边还没嚼烂,那边又扯下一个鸡大腿往嘴里塞。
可爱的糊涂美人! 可爱的肘子肉!可爱的烧鸡!
就在我对糊涂美人肘子肉烧鸡发出赞叹时,他们四个已把做好的饭菜端了进来。
热气腾腾,香气四溢。
我不得不佩服老夫子的厨艺,凭色香味就可以断定,这几个菜一定鲜美无比。
陈山月眼尖,一进屋眼睛就盯上了肘子肉和烧鸡。
她问:“守义,肘子肉和烧鸡谁送的?”
“糊涂美人。”
“她为什么送烧鸡和肘子肉?人呢?送给谁的?”
陈山月一连串发问,让我好笑,故意说:“她家东西多呗。她送给谁的,她没说,我也不清楚,估计是送给秀才的。”
陈山月咕嘟着小嘴没搭腔,鲁余粮迫不及待地说:“守义开什么玩笑,糊涂美人怎么会给我送东西?要送也是送给老夫子的。”
老夫子沉得住气,他把肘子肉和烧鸡拿到桌子上笑着说:“那我真得谢谢糊涂美人了。这年头儿,年三十能吃上肘子肉和烧鸡,我们都成了皇帝了,真是鸿福齐天也。”
倪春萍憋了半天没抢上话,我以为她也要大发酸意,谁知她的话非常得体,道:“陈嘉良说得对,年三十能吃上肘子肉和烧鸡,这个市里也没几家了。胡玉珍给你们送来,是你们的福气。感谢我们的阔夫人,我和山月借光了。”
我带头鼓起了掌,寝室里响起了兴奋的掌声。
我给大家杯子里到满了酒,大声说:“哥哥姐姐们,有老夫子大哥做的鱼和肉,有糊涂美人的肘子和烧鸡,有香甜的美酒,这是多么丰盛的年三十啊!让我们共同举杯为我们伟大、繁荣、富强的祖国干杯吧!”
干杯——寝室里响起了不间断的干杯声。
这顿年夜饭我们吃得十分愉快,酒也喝得尽兴。大家红光满面,喜笑颜开,让我暂时忘记了思乡之痛,思亲之悲。
我们就像三个毫无心肝的人,尽情和陈山月倪春萍说笑着。
这顿饭吃的时间很长,直到外面响起稀稀落落的鞭炮声,陈山月和倪春萍才张罗着回家。我装作不胜酒力,从桌子上一站起来就趔趔趄趄摔倒在炕上。老夫子和山东秀才各得其所,一人一个送得美人归。
宿舍里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思绪万千,悲从中来,真想放声大哭,嚎啕大哭,哪怕哭个昏天黑地,但我还是忍住了,叹息一阵,稀里糊涂睡着了。
大年初一,晴空万里,蓝天一碧,虽然风是寒的,但是太阳已经爬起来了,它的光映着白雪的光,亮得刺人眼睛,照得我们的寝室一片明亮,同时,零星的鞭炮声,也和太阳一样,提醒着我们,我们活过了一年。
我们把除夕的饭菜简单热了热,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大年初一的早餐,就商量如何拜年。我们决定先去给郑老师拜个年,然后自由行动,并强调晚间无论早晚都必须回寝室。
我们敲开了郑老师家大门,老师似乎早有所料,满面春风地把我们让进客厅。我们向老师和伯母问候春节好,恭敬地行了礼。丹丹调皮地对我说:“叔叔,你还没向我问好和行礼呢。”我们一阵大笑。我抱起丹丹亲着她娇嫩的小脸蛋,丹丹左躲右藏地喊着:“叔叔胡子扎人,我不要亲了。”
我们又是一阵大笑。
老夫子和山东秀才陪着老师唠着过年嗑儿,讲着班上的一些话题。我发现老师虽面带高兴,却好像强装出来的。不知道她美好的笑容后面,隐藏了多少辛酸。
我张罗着向老师告辞,老师百般留我们一起吃饭,丹丹也拉住我,耍娇使赖不让走,最终,我们还是离开了老师家。
到了老师楼下我们分开了,老夫子拿着寝室和厨房钥匙,他说去看个朋友,四点钟肯定回寝室,要做好菜等我们回去喝酒。秀才去南山矿看两个同乡,我则去了表姐家。
我自从进了教师培训班,就很少去看表姐他们了,不是我忘恩负义,我是不想给他们增加额外负担。东北人讲究亲情,表姐对我就跟她亲弟弟一样。我每次去,她都尽可能地给我做好吃的,在这饥饿的岁月里,实在难为她了。
一进表姐家,表姐全家人的脸上都堆满了笑。大宝拉住我舅舅长舅舅短地问这问那,囔哧鼻子表姐夫说:“我以为你小子不来了呢,这么快就把姐夫给忘了。”
“怎么会呢?忘了谁也不会忘了姐夫。”
“这就对了,你可别拿豆包不当干粮,驴粪蛋还能发烧呢!”
表姐接过表姐夫的话说:“你就等着发烧吧。等你发烧那会儿,全家人还不都得饿死。”
表姐似乎觉得大年初一说这话不吉利,对我笑了笑,就去做饭了。表姐夫感到丢他面子,对着厨房喊:“老娘们就是老娘们,头发长见识短,大过年的胡咧咧。天老爷还饿不死瞎家雀呢!”
我看了看囔哧鼻子表姐夫,他明显瘦了,虽然还是大头大脑,却少了以前的精神,黑黄的脸上又新刻了几道深深的皱褶,看上去很沧桑。
我和表姐夫闲扯一会儿,表姐就把菜端上来了。
有鱼、有肉,又搭配了几样蔬菜,把不大的桌子摆得满满的。
表姐脸上带着无奈说:“守义,凑和吃吧。大过年的连只鸡都没买到。”
表姐夫说:“你小子高兴吧,还是你表姐对你好,这鱼和肉还是你表姐特意为你留的呢。”
我相信表姐夫说的是实话。我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表姐,看着表姐夫和大宝,我没说什么,面对如此亲切的一家人,客套话还有用么?
表姐的菜做得很有滋味儿,可我实在没有食欲。勉强喝下表姐夫强行倒的两杯酒,就感到有了醉意。我又和表姐表姐夫聊了一会儿,就怀着歉意告别了表姐一家人。
千家万户彤彤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新春伊始,万物更新,似乎我们的心情也应该有所更新了。但是,春节分的那点东西,我们虽然舍不得吃舍不得用,还是渐渐少下去了,小秋收的菜也所剩无几。面对着空寂的都市、苍茫的雪野,我们甚感无助。此时,大家虽然不说,但心里都在期盼,盼着倪春萍和陈山月到来。她们啥时来了,都会带点好吃的,除了吃,还有她们的笑声。那是青春的笑声,在灰暗的日子里,除了带给我们生命的欢娱,也让人从那无忧无虑的笑声中,找到了人生的希望。
倪春萍不经常来,即使来了也不多待。我看出她和老夫子的故事,好像只有开头没有结尾。老夫子的心情可想而知,不是长吁就是短叹,或者龟缩在宿舍一角。我和秀才开导他、劝他,让他主动一些,他摇着头道:“没用啊,我兜里一分钱一斤粮票都没有,不用说上她家拜访,就是想和她吃顿饭都办不到。唉,天绝我也!”
我和秀才无言以对,兜里有限的那点钱和粮票,委实无法赞助老夫子的爱情。
正月十二,老夫子突然决定回家,我和秀才没有阻挡他,他家也不远,确实应该回家换换心情了。我们只是担心,他一走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但他肯定地告诉我们,开学时一准儿回来。
老夫子走的第二天,谢玲风尘仆仆地回来了。
看到谢玲,我高兴得无法形容,我问她,“还有几天才开学呢,怎么不等开学时回来?”她说了一句,“人家不是想你么!”就红着脸扑进我怀里。
谢玲提前回来,陈山月和秀才都为我高兴。秀才说,“守义,谢玲对你的情意,千斤难买,你可不要辜负人家呀。”陈山月也说,“你小子施了什么魔法?谢玲的魂儿都在你身上了。”
我反诘道:“陈山月,你魂儿难道就没在秀才身上?”
陈山月看看秀才,欲言又止。
我和秀才露出得意的微笑。
谢玲带回不少好吃的,我们美美地吃了两顿。
正月十六开课了,同学们也基本都回来了。我和秀才担心的老夫子也返回了学校,他看上去精神还好。倪春萍和老夫子还是有说有笑,在她脸上找不到一丝尴尬。糊涂美人一点也不糊涂,私下问我,烧鸡好吃么?我回她一个感激的微笑。
郑老师有点精神不佳,面对同学,不得不露出笑脸。她告诉我们,教育科有了新精神,今年课程从高一课本讲起。这对有的同学是比较深的,但也只能如此,希望同学们加倍努力,上课时注意听讲。
高一课本,对我和谢玲,秀才和陈山月来说,并没有多少压力,我们依然有时间去图书馆,也有时间深化我们的爱情。但可恶的肚子却经常干搅我们,虽然它让我们控制得异常干瘪,但还是会出现不依不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