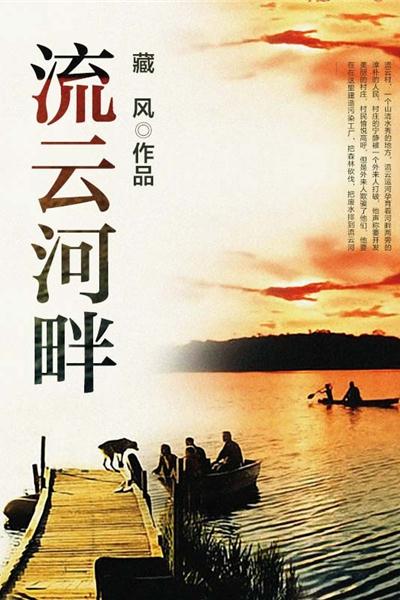自从接受了糊涂美人的恩赐,我心里就没有一天安宁过,我觉得这样对胡玉珍太残忍了,面对一个温顺善良胸无城府的女人,我这样做太损了。后来,糊涂美人又约过我两次,我都借故推托了。
有一天谢玲对我说她很饿,我带她去吃面条,我们找了一家饭店,排了一个小时的队,终于买到了两碗面条。当我掏钱拿粮票时,谢玲问,“哪来这么多粮票?你粮票不是只剩下几斤了么?”我说是表姐给的,她有点不相信,但也没追问。往回走的路上,谢玲心情郁闷地告诉我,她爸来信了,信中说她爷爷在河南老家饿死了。他让谢玲放暑假和她妈妈回河南,去把她老家的奶奶接到东北来。
“你爸爸为什么不回去接?饿死的可是他爹呀。”
“我爸整天忙着训练民兵,国家怕苏修打过来,连爷爷死了都没让他回去。”
听了谢玲的话,我久久没有出声,脑海中浮现出一群饿得枪都背不动的农民,一个个低头耷拉脑保卫祖国的画面。
过了几天,郑老师通知同学们,“由于不能正常上课,教育科决定放五十天暑假,再过两天就放假了。也就是七月一日放假,八月二十一日开学,同学们有什么打算和安排都早做好准备。”
听完老师的话,同学们互相打听各自的安排,有的说回家,有的说留在学校,有的说去挖煤。老夫子问我有什么安排,我告诉他没有具体打算,过两天再说吧。
糊涂美人插话:“一定是和谢玲回家了。”
我看了她一眼没吱声,谢玲生气地说:“回不回家与你有关系么?”
糊涂美人红了脸,说道:“当然和我没关系,我关心你们还不可以么?”
谢玲说:“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的李所长吧。”
我知道谢玲的火气由何而来?可能是感到糊涂美人对我太好了。
我告诉糊涂美人:“谢玲回河南接她奶奶,我现在还没有决定去哪儿。”
糊涂美人脸更红了,本来想对谢玲发火,听了我的话,再没说什么。
第二天天气晴朗,我在食堂买了两个小馒头,就和谢玲去了我们经常去的郊外的白桦林里。这是一片美丽的白桦林,棵棵白桦碗口粗细,在天空为我们擎着一柄柄大伞,树下,铺着一层羊胡草,这种草,真像羊胡子一样,又细又柔又有韧性,踩上去软软的,躺上去绵绵的。我和谢玲一进入白桦林,便疲倦地躺在羊胡草上,享受着树叶间筛下的或大或小耀眼的光斑,感受着白桦林里的清纯宁静。人到了这种地方,都变成了神仙。但是,我们却没有神仙那样宽大的心怀,无情无绪地躺在羊胡草上。
谢玲温顺地躺在我的胳膊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
“谢玲,你放心回河南吧。”
“你也回家吧,看看你爸爸妈妈、弟弟妹妹,你不总说想他们么?”
听完谢玲的话,我心里非常难受,我何尝不想回家呀,但我能回去么?想到这里,不由长叹一声。
谢玲可能以为我为分别叹息呢。
饥饿,饿得一对青年男女,连谈情说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们躺在那里,只是不想耗费太多的体力。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第三天,谢玲被他父亲的一个佳木斯的战友接走了。他们先坐车先去佳木斯,在佳木斯乘船回汤原,再和她母亲一起去河南。我要把她送到佳木斯,谢玲说什么也不让,说那样怕她自己也走不了。
宿舍空荡荡的,又剩下老夫子秀才和我三个人。他俩决定哪也不去,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心里千头万绪,乱麻一样梳理不清。思来想去,我决定去老师家,让她给出个主意。
到老师家后是伯母开的门,丹丹看见是我就喊:“叔叔,妈妈,叔叔来了。”老师从卧室笑着走了出来。她刚洗过头发,还没来得及梳理,黑黑的长发瀑布一样飘洒在脑后,衬托着她苍白娇美的脸。我从没发现老师这么美,那一刻简直看呆了。
老师发现我不管不顾地看着她,一边披外衣,一边不经意地问:“守义、你来得正好,你这个暑假有什么打算?”
“能有什么打算,去野外搞点野菜,一凑和五十天就过去了。”
“老去弄野菜也不是办法。现在野菜都老了,总吃会吃出病的。这个暑假,我带丹丹去我大舅那儿,你如果能去最好了。去掉我需要学习的十天时间,连来带去我们可以在那里待上四十天。我大舅在水库看鱼打鱼,家中就他一个人。水库里有鱼、有虾、有蛤蜊,山上野菜也多,那里肯定比我们这里好维持。家里省下点粮食也能让我母亲吃几顿饱饭。为了我和丹丹,我母亲总是不吃饱。”说着,老师的眼圈红了。
听完老师的话,我非常激动,马上说:“老师,我去。”没等老师说话,我着急地接着问,“老师,什么时间走,明天走好么?”
看我着急的样子,老师笑了,告诉我明天她去教育科安排一下,后天一早动身,又嘱咐我去水库的事儿不要告诉老夫子和鲁余粮,人去多了,大舅那儿地方小,没地方招待。
吃饭时,伯母告诉我水库如何如何好,鱼虾多得了不得,她如果能走动,也要和我们一起去不可。
去水库那天早晨,我起得很早。我把两件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品放在包里,喊醒老夫子和秀才,撒谎说去银春我大哥那里,就匆匆离开了。到了老师家,老师和丹丹准备好了。我们把带的东西绑在自行车上,让丹丹在车上坐好,告别了伯母,我们就踏上了去水库的路。
鹤岗有好几座大水库,我们去的是鹤岗的五号水库。五号水库在南山矿的西南面,大多都是蜿蜒的山路,但还不算难走。我推着自行车,边逗丹丹边和老师说笑着,心情轻松愉快。刚出市郊时,还能看到一些采野菜的人,进入到了山区,就很少看到人了,好像这条路专门是为我们修的。但路也越来越狭窄了,推着自行车勉强还能行走。大约走了三十里路,才算进入到真正的山区了。山坡上,苍松古树直插云天,山洼里一片片白桦林,一排排水冬瓜,一丛丛托盘儿,还有这一棵那一棵的暴杩子……暴杩子也叫暴杩丁香,此时正是盛花时节,一丛丛一簇簇,枝头开满白花,若云若絮,在绿野的衬托下白得耀眼,把奇异的香味儿散发出来,闻上去心清气爽。大山里,除了暴杩子美得打人眼睛,山坡上,更有红的野百合黄的金针菜蓝的马莲花粉红的石竹花……各种野花,大花小朵,将山野装点得如同锦绣,让人目不暇接。除了暴杩子散发着强烈的香味外,各种野花也互不相让,清爽的风将所有的香味儿融合起来,又分散开来,闻起来泌人肺腑。现在有一个词儿,叫负氧离子,说能兴奋神经。当时不知道这些,只觉得一进入山中,就兴奋,就像走向回家的路一样,让人全身都想飘起来。丹丹坐在自行车上,乐得又喊又叫,一会儿要这朵花儿,一会儿要抓那只蝴蝶儿。老师也非常高兴,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岁。大自然的景色使她忘记了烦恼,逝去的青春在无所顾忌中又显露出来,她跟在自行车后,一会儿给丹丹采花,一会儿给丹丹捕蝶,举手投足,活脱脱就是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我们一路欣赏着美丽的山野景色,一边往山里行走,大约又走了十几里,老师告诉我,再有二十多里就到水库了。一路兴奋,丹丹开始昏昏欲睡,我停下自行车,把丹丹抱下来。对老师说我们休息一会吧。老师的脸红扑扑汗津津的,白底兰花翻领衫已被汗水溻湿了。
我们在路旁的小河边坐了下来。小河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清澈冰凉。我们痛痛快快地洗了洗脸,喝足了淳如甘露的泉水,顿时感到精神了很多。丹丹也不困了,她吃了几块饼干,就跑到一丛野百合前折花,她费了很大劲儿折下两朵,一定要给老师带上一朵,老师戴上后,她围着老师转了两圈说:“妈妈戴花真好看,叔叔也戴一朵。”丹丹说着就要给我戴花,我抱过丹丹说:“叔叔不戴花,叔叔是男人。”丹丹不依不饶,说:“叔叔骗人,男人怎么不戴花?爸爸和妈妈的照片,爸爸就戴花。”听完丹丹稚气的话,我抬头看看老师,老师脸上露出了一丝哀怨,勉强对我笑了笑,说道:“到水库还很远呢,咱们走吧。”
我把丹丹抱上自行车前大梁,对老师说:“你也坐在自行车吧,还能扶着点丹丹。”老师不肯,我好说歹说老师才坐到自行车上。
我推着坐着两个人的自行车虽然累,但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支承着。下午两点多,我们到了五号水库,找到了渔业队,也找到了老师的大舅。
老师的大舅是个典型的山里汉子,五十多岁,皮肤黑红,风吹日晒的脸上过早地刻上了皱纹。看到我们,老师大舅很兴奋,抱过丹丹说:“丹丹长这么大了,还认识舅姥爷么?”丹丹吓得要哭,老师对丹丹道:“丹丹,这是舅姥爷,快叫舅姥爷。”丹丹一声不发。老师将我也介绍给了她大舅,说:“这是我学生张守义,陪我们一起来的。”大舅笑哈哈地说:“这孩子长得精神。好,我安排一下咱们就回家。”老师对我说:“我大舅,你也叫大舅吧。”老师的建议正合我意,我叫了一声“大舅”,大舅乐哈哈地对我点点头,认了。
渔业队是建在水库旁边的一座砖瓦房,大舅把我们让到屋里。屋里坐着十多个年龄不一的汉子,大多都在吞云天吐雾地吸着旱烟,整个屋子都被烟雾挤满了。我们进屋后,大家转过脸来,好奇地看着我们。大舅介绍了老师和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来这里过暑假的。这些山里汉子,很善良,朝我们露出了友好的笑容。大舅对一个三十左右的黑脸汉子说:“李队长,我带他们回家了,晚上再来。”李队长说:“外甥女来了,不要急着回来。”转向一个年轻瘦子说:“王老三,去囤子里拿条鱼,挑大的,让老赵拿回去招待外甥女。”叫王老三的年轻人答应着跑了出去,一会儿,就拎回一条四五斤重活蹦乱跳金黄的大鲤鱼。
大舅提着鲤鱼,领着我们回家了。
大舅的房子离水库不远,建在山坡上,旁边还有五六户人家,各家的房子不挨不靠,每家都有一大块园子,将整个山坡占住了。大舅的园子里除了种一些苞米高粱等大庄稼,还有一些青菜,绿油油的长得十分可人儿。院子里也打扫得很整洁,烧柴垛摆得见方见角。大舅房子是座草房,墙抹得很光,显得质朴厚重。大舅的门没锁,打开房门,小屋里的一切尽收眼底:一铺炕,一个锅台,锅台连着炕,中间搭着一尺高的墙台,墙台上放盏煤油灯,炕上摆着烟笸箩,炕稍立一个被褥架,上面摆着两铺麻花被。地下一个木箱,箱子上放着盆碗筷子,旁边还立着一个小炕桌,这就是大舅小屋的全部了。
大舅笑着说:“这就是舅舅的家,小了点,一个人住也用不了多大。”大舅的话流露出满足和乐观。
老师将丹丹放在炕上,打开提兜拿出两盒罐头说:“大舅,这是我妈让我给你带的罐头,现在市里啥都买不到了。”老师显得不好意思。
大舅没在意,乐呵呵地说:“住这里谁还吃罐头?新鲜的东西还吃不过来呢。对了,我姐身体还好么?”
“我妈身体还行,只是腿还是老毛病,关节炎,不然也来了。”
我见大舅和老师唠家常,拿出毛巾抱起丹丹对老师说:“我带丹丹去洗洗。”
“出门沿这条道一直走,百十步就是水库了,洗衣服洗澡都行。”大舅告诉我。
我抱着丹丹顺着砂石小路,来到水库边上,抬眼一看,眼前的大水库,浑然到了仙境。
碧波荡漾的几十里水面,夕阳中波光粼粼,泛出万点金光,一些水鸟在水面盘旋着。水库四周青山围绕,将整个水库衬托得就像一面镜子,青翠朦胧的远山和霞光,在镜子中投下浓重的倒影。
靠近大舅小屋的水库边上,是一片大大小小的卧牛石,有的浮出水面,有的趴在水底,真像一群牧归的水牛,静静地在水中洗澡呢。一块靠近岸边的黑赭色的大卧牛石,上面可以躺上五、六个人,就像一个大石床。我把丹丹放在“石床”上,把自己脱得只剩一条裤衩,把丹丹全身脱光,抱着丹丹一步步走进水中,泡在被太阳晒了一天热乎乎的清水中。水不足一尺深,清澈见底,柳叶般大小的鱼在水下穿梭来往。
丹丹喜欢得笑个不停,我俩相互撩水、嬉戏,玩了一会儿,又开始抓小鱼。小鱼很难抓,灵活的在石缝中钻来绕去,我和丹丹四只手也堵不住它们,丹丹露出失望的神色,呶着小嘴道:“叔叔,不抓这些破小鱼了。”
我安慰她:“叔叔一定给你抓住这些破小鱼。”
我和丹丹专注地抓那些难抓的破小鱼儿,老师来到跟前才发觉,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老师说:“这水真好。”
老师看着我说:“真羡慕你,我要像你这么大多好。”
我愣了愣,转换话题道:“老师,你也洗洗吧。”
“我不洗了,大舅把鱼都炖好了,等我们吃饭呢。”
我和丹丹穿上衣服,老师蹲在水边洗把脸,我们回到了小屋。
大舅见我们回来,放上炕桌。大舅掀开锅盖,霎时间鱼和苞米面大饼子的香味儿飘满了小屋。锅里炖的是那条大鲤鱼,锅的四周贴了一圈黄灿灿的苞米面大饼子。看到这些,猛然间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回龙崴子,想到父亲的房子,父亲的扳罾网,妈妈炖的鲤鱼和贴的大饼子……感到特别亲切。
大舅将整条鱼盛在一个大瓷盆中,放在炕桌中间,又铲了一盘大饼子放在旁边。肥美的鱼肉,香甜的大饼子,让我们食欲大开。大舅边哄着丹丹边给她挑不带刺的鱼肉,而我和老师也顾不得客气了,顾不得有刺儿没刺儿,就往肚子里吞咽。丹丹弄得满脸油污,还舍不得放弃盆里的鱼肉。大舅看我们吃得这么香,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说道:“咱这大水库,别的没有,吃鱼管够儿。你们爱吃,大舅明天再往回带。”
大舅如此说,我和老师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吃完饭,老师问大舅:“山上的野菜多不多?我们想在这里过完暑假,省下点粮食也好让我妈吃几顿饱饭,城里的日子太难了。”
大舅听了老师来意,说道:“什么野菜?在舅舅这儿用不着吃野菜。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粮,那个箱子装得满满的都是粮。再说了,咱这个大水库就是个聚宝盆,里面装满了鱼和蛤蜊,就怕你们吃腻了。我和李队长说说,让你们去大沙滩。你们没事儿就在那儿打鱼捞蛤蜊,可好玩了。”
听了大舅的话,我和老师都很高兴。大舅又告诉我们,他晚间在渔业队住,不能回来。现在,有不少逃荒的都来水库偷鱼,渔业队的劳力全成了打更的。大舅又叮嘱我们,晚间睡觉一定要把房门关好,把大门也关好、插好,这里靠着山,晚间常有黑瞎子和狼跑来找吃的。大舅说完就回渔业队去了。
大舅是个爽朗的山里汉子,在他面前,一点都不用拘束,很随便,大舅一走,小屋里只剩下了老师、丹丹和我了,一时间,这逼仄温暖的小屋,倒将我们关得有些不自然了。我和老师几乎同时看看窗外,看着黄昏的光线越来越浓重,又回头看看小炕,看到这铺能睡三个人的小炕,我们又互相对看了一眼,一时间,不知对方心里都在想什么。
天很快就黑了,按照大舅指点,我到外面关好了大门,又回屋关好房门,老师点亮了那盏油渍斑驳的小油灯,把被褥铺好。丹丹兴奋了一天,老师刚将她放到炕中间,就呼呼睡着了。屋里空气不流通,关上门后更加闷热,炕也烫手的热。我身体也是燥热难捱,虽然不自然,还是红着脸脱掉了外衣,只剩下背心和裤衩。老师也是一脸汗水,见我脱衣服,也脱掉了外衣,我偶一回头,看到了她脱得也只剩下背心和短裤了,感觉头脑“嗡”地响了一声,我不仅看到老师脱了外衣,还看到了老师白背心包裹的胀鼓鼓的乳房,粉裤衩包裹的圆圆的屁股……见我回头,老师脸更红了,轻声说:“守义,睡吧。你睡炕头,我睡炕梢。”
我听话的答应一声,吹熄了小油灯。
小屋一片漆黑。
黑暗中,感觉心里轻松了许多,我相信,老师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躺在炕上,我满身疲乏,却睡不着,整个心思全被老师包围了,满脑子都是刚才老师脱衣服的形像,饱满的乳房、浑圆的屁股……那几个圆儿,圆得我脑海中一片晕炫。
此时此刻,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和牛淑芬的初恋,脑海里全是圣洁,干净得没有一点肉欲的想法;我和谢玲的爱恋,曾经有过肉欲的感觉,却被我用理智战胜了;现在,和老师一起躺在这温暖的小屋中,听着老师的呼吸声,闻着老师散发出来的异样的体香,我整个心思都集中到了一处,被老师吸引过去了,甚至可以说,潜伏了十七年的欲望,在这一刻被老师引爆了……我拼命压抑着自己的欲望,但是,越压抑那股火烧得越旺,烧得口干舌燥,我真想跳起来,过去抱住老师,用她的湿润,浇灭我满身的欲焰,但是我压抑住了自己。我翻来覆去在炕上折腾着,一会儿强压呼吸,一会儿叹息连连,就在我折腾时,耳朵也出奇的好使,我听见老师也在翻来覆去,也在叹息连连。老师的动静,更加强了我的欲火,那个东西不甘示弱,随着我越压抑它,挺得越加坚强,最后,我只能安慰它,轻轻一碰,它就像一匹野马似的挣脱束缚,呼啸奔出……
一股腥腻的味儿在屋子里弥漫开来。
这一过程,虽然都是在黑暗中发生的,一旦平静下来,却让我心里充满了悔恨。我骂自己,我是多么可耻,多么龌龊,和我躺在一个炕上的是我的老师啊,是关怀我爱护我的老师,她就像圣母一样圣洁,我的所有想法,都是对她的亵渎……如果老师这时问我什么味儿时,我相信,我会找个地缝儿钻进去。
老师虽然喘息粗重,并没有问。
老师如此,让我更加不好意思,我强忍着羞愧感,感怀着老师的伟大,老师的美好……但刚一想到老师,那股劲头儿又冲上来了。
我赶紧下地,轻轻推开门,在夜的冷风中站了一会儿,打了一瓢水洗了把脸,把身子也洗了一下,在冰冷的刺激中,这才平静下来。我回到屋中,只听老师轻声说:“守义,快睡吧。”
我轻声“嗯”了一声,躺在炕上,不知不觉睡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