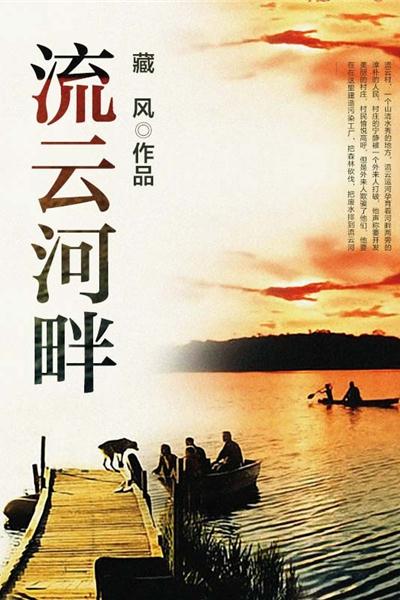离开了宿舍,刚走出门外,糊涂美人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守义,你是不是有个表姐夫叫李国林?”
“我表姐夫是叫李国林,什么事么?”
“出事了,他让派出所抓起来了。”
“究竟怎么回事儿?”虽然我有预感,囔哧鼻子表姐夫早晚会出事儿,可没有料到会这么快。
糊涂美人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我。
糊涂美人说,昨天李所长和几个民警去星火屯执行任务,半夜回来路过二道岗时,看到四个人背着东西从山上下来。那几个人鬼鬼祟祟,躲躲藏藏,他们就停车去检查他们。见有车停下,那几个人扔下东西就往山里跑。李所长他们开了枪,才把他们镇住。一检查他们背的东西,竟是新杀的驴肉。李所长把他们关进了看守所,经过审问,一个叫李国林的说他老婆有病,不能告诉他老婆,还说有个表小舅子叫张守义,在教师培训班读书,事情怎么处理通知他。
糊涂美人的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如果按偷杀耕畜破坏生产论罪,少说也得判个三、五年的,真要如此,不要说囔哧鼻子表姐夫,就是表姐和大宝,在这饥饿的年月里还能活下去么?
糊涂美人看我急得团团转,说道:“守义,不要着急。先去我家见见李所长,也许会有办法的。”
当我第一眼看到糊涂美人丈夫李所长时,心里隐隐感到囔哧鼻子表姐夫或许有救了。
李所长看上去年近五十,身材不算高大但很结实,一张黑红的脸庞,上面的淳朴、善良隐约可见。虽然刚见面,我就感到这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李所长见糊涂美人将我带来了,没打官腔也没摆官架子,忙着沏茶倒水,拿烟拿水果。
我冷静了一下问道:“李所长,听胡玉珍同学说我表姐夫被你们抓了,问题严重么?”
“你是说那个偷驴的李国林,他真是你表姐夫?他的问题很严重。”李所长平静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说得很肯定。
我斟酌再三道:“李所长,请你无论如何也想想办法把我表姐夫放出来。他是个本份的老工人,是个粉匠,以前从没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儿。要不是饿疯了,他是不会带着孩子走下道的。如果他判刑了,我有病的表姐和孩子都没法活了。”
糊涂美人一边帮着腔:“李所长,你一定要帮这个忙儿。不是饿疯了,谁会带着孩子干这事儿呢,你说是不是?你们当官的,在困难的时候,就更应该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啊。张守义同学没少帮我,如果没有张守义帮助我学习,我根本跟不上学习进度。不就杀头破驴么?我要没饭吃我也去杀呢,再者说了,放不放人还不就是你一句话。”
糊涂美人对她丈夫又戴高帽又是耍娇,我感激地望了她一眼。
李所长被妻子弄得啼笑皆非,当着我的面,好像不知怎样跟妻子解释才好,吸口烟说:“你俩不用讲了,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偷驴偷耕牛,这是破坏生产罪,国家一直管得很严格。再说了,现在挨饿的又不是他一家,大家要都这么干,咱们国家的牲畜还能剩下一头么。事情既然发生了,你们也不用着急。我先写个条子,守义同学拿着条子到看守所把两个孩子领回去。两个大人的事儿,我和局里商量商量再定。”
我拿着李所长特赦令一样的三寸批条,谢过李所长匆忙去了看守所。
看守所一胖一瘦两个民警,看到李所长的纸条对我很友好,他们让我在门外等候,他们进去领孩子。为了能看到囔哧鼻子表姐夫,也是好奇,我好说歹说,才和他们一同进了看押犯人的房间。
看守人员打开房门,一股尿骚气汗臭气混合在热浪里扑面而来,几乎把人扑倒。胖民警对我说:“快进去把两个孩子领出来,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
我迎着那股骚臭味儿走进了监房里。
这里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不足二十平米的一个筒子屋,挤满了蓬头垢面的犯人。犯人们,成串的汗水强硬地挤开了污垢的面皮,檐前滴水一样滴答着。一个尿桶孤傲地立在墙角,显示着无人敢挤的威严。大小不一的蟑螂和潮虫,在地上穿梭般爬来爬去,有的毫不客气就爬到人身上,舔食着带有咸味儿的臭汗……就在我熏得要晕倒时,大宝哭喊着:“舅舅——舅舅——”我循声望去,看到了大宝和囔哧鼻子表姐夫,卷缩在一个墙角,和他们卷缩在一起的,还有一大一小两个人,可能就是囔哧鼻子表姐夫说的,是他的合伙人王二和王小二了。
囔哧鼻子表姐夫一见我就掉下了眼泪,让我无论想什么办法也要把他弄出去。我没过多地安慰表姐夫,告诉他我会想办法的,直到带着大宝和王小二走出监房,我才深深地喘出一口气。
我本想把王小二送回家,却被他拒绝了。王小二比大宝大一两岁,瘦小干枯,但很倔犟,他说他能回去,回去想办法和他妈妈找人把他爸爸弄出来。望着王小二的背影,我苦笑着摇摇头。
大宝一打开院门,我就见到表姐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院里转个不停,她好像昨晚一晚没有睡觉,眼圈黑黑的,头发也没梳,样子很憔悴。她吃惊地看了我和大宝一会儿,紧接着死死地搂住大宝,发出一连串问话,大宝只是哭,什么也回答不了。我关上大门,把这母子俩推到屋里,表姐这才感到出了什么问题,她推开大宝,两眼直直地盯着我问:“守义,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平静地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以为她会嚎啕大哭,没想到表姐很冷静,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叹口气说:“我知道早晚会出事儿,劝他不要干了,他就是不听。死活就认准这一门了,这也是该着有这步灾呀!”
我安慰表姐:“事情发生了,后悔也没用。你放心吧,我会想办法把姐夫弄出来的。”我说得很肯定。表姐虽然怀疑我的能力,但我的话对她还是起到一定的宽慰作用,她说:“守义,表姐就靠你了。想什么办法也要把你姐夫救出来,在那里还不被折磨死。”说完,表姐流下了眼泪。
表姐像忽然想起了我们还没有吃饭,着急地说:“看,我都忘了给你们做饭。”表姐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急匆匆走进厨房。
我问大宝:“是不是早饿了,在那儿吃没吃饭?”
“吃了,早晨给一个小窝窝头,中午也给一个小窝窝头。还有人上来抢,爸爸护着才没有被抢走。”
我没有再问大宝什么,一颗幼小的心灵所经历所看到的还能是什么呢?大宝太累了,见我不再问什么,说了句:“舅舅我累了。”躺在炕上就睡着了。
我头脑很乱,思索着发生的一切,想通过什么办法才能把表姐夫弄出来?最后想到了糊涂美人,我知道,也只有通过糊涂美人儿,救出表姐夫才有希望。但怎么去求糊涂美人呢,这让我颇费周折。
就在我胡思乱想时,表姐把饭菜端进来了。大宝睡得很香,我和表姐没有喊他。我看着桌子上两盘菜,有一盘居然是驴肉。面对着这惹祸的驴肉,我感慨万端、莫衷一是。表姐默默地陪着我吃饭,不停给我夹菜,唯一的话就是劝我多吃点。吃过饭她从箱子里拿出五十元钱,不容分说塞进我兜里,表姐说:“守义,你表姐夫全靠你了。不过你也不用着急,能不能出来就看他的命了。老天爷怎么这样对待他呢?”
为了让表姐放心,我讲得很仗义,告诉她,我一定能将表姐夫弄出来。
离开表姐家,我脚步机械地往宿舍走着。回到宿舍我没把发生的事告诉老夫子和秀才,他们也没问。第二天下课时,我去办公室把表姐夫的事情讲给了老师,她着急地说:“守义,这不是小事儿,得尽快想办法把他弄出来。”
“我已经去找了胡玉珍丈夫李所长了,他没有肯定答复,只是写了个条子给我,让我去看守所把孩子领回来了。”
“要不我去找一找李所长,也许能比你管用些?”
“不行,你去找李所长师出无名。尽管比我管用,也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猜疑,你就不要去了。”
老师点点头儿。
上课时间到了,我们对看了一会儿,老师亲切地叮嘱我注意身体,事情总会解决的。老师说完这些,目送我离开了她。
下午放学时,我快步追上了糊涂美人。她故意绷着脸问我:“张守义同学,有事么?”她装腔作势的样子,看上去很滑稽。
我忍不住笑着逗她:“能有什么事儿,就想多看你一会儿。”
她一脸绯红,忸怩了一会才说:“我可不敢让你多看,时间长了你会嫌烦的。”
听她说出这句话,我不敢继续调侃了,心里提醒自己一定要把握分寸,对她既要用上又不要被粘上,这就颇费心思了。
我故作正经地说:“玉珍姐,不说这些话了。我想请你吃饭,你能去么?”
“好啊,吃饭怎么不能去?你是应该好好请请姐了。”糊涂美人没有半点推脱,和我去寻找饭店。
我们一连找了好几家饭店,她都不满意,她倒不是对饭菜和卫生有什么挑剔,只是嫌人多。进家饭店,只要有几个人在吃饭,她就说不行。最后找到一个只有两个服务员,又没有人吃饭的饭店,才算满意了。我要了四个菜,还有一壶酒,然后在饭店找个角落两人坐了下来。时间不大,服务员端上了饭菜。我给她倒上了一盅酒,她说不喝,可还是端了过去。偌大个饭店就我们两个人,我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委实觉得无话可说,又不能不说,只好一个劲儿劝酒让菜,不停地往自己嘴里倒酒。糊涂美人被我的热情感染了,自觉不自觉地找到了女主人的感觉,开始热情洋溢地为我倒酒夹菜,同时,火辣辣的眼睛,也无所顾忌地在我脸上扫来扫去,说话的声音也提高了。
“守义,你请姐姐吃饭,我知道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三杯酒下肚,忘了提醒自己,顺口说:“玉珍姐,我要真是黄鼠狼,一定要吃掉你这只鸡,我总在想,味道一定很美。”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但已经收不回来了。果然,糊涂美人接住杆便往上爬,说道:“守义,姐姐就盼着你来吃呢。你什么时候想吃都可以,能被你吃掉,姐姐也没白活这辈子。”
我想收回那句话已经不可能了,只好一边顺着她一边扭转话题,说道:“玉珍姐,我从心里想把姐姐吃掉,可李所长会答应么?”
我这句话说到了她的要害,她半天没吱声,端起酒盅就要喝酒。我伸手拿过酒盅对她说:“玉珍姐,不要再喝了,让李所长看到你喝醉的样子可不好。”
“唉——”她长长地唉了一声,我以为她会就此打住。哪知道,她一下子握住了我的手,握得紧紧的。两眼盯着我说:“守义,你先不要管李所长答不答应,你答应就行了。姐姐有的是办法,保管把一切安排好。一定让你吃个够,你就是把姐姐活吞下去,我也不后悔。”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感到无路可逃了,为了能救出囔哧鼻子表姐夫,只有顺着她的话说下去。我看了一眼无所事事的服务员,轻轻抽出我的手,亲昵地小声说:“玉珍姐,谢谢你看得起我。只要你安排好,我保证为姐姐献出一切。”
说这句话时,我感到自己的脸在发烧,糊涂美人的脸也开始红了,使劲掐了我一把说:“净胡说。”
我接着说:“这事不能操之过急,如果让李所长知道了,我表姐夫就别想出来了。”
“这事你放心,用不了几天,我就会让他乖乖地把你表姐夫放出来。”
“你有什么办法?”
“不告诉你。女人要是治服不了自己的男人,还叫女人么。”
离开饭店时,夜色已经笼罩了这座煤城。稀稀落落的路灯,无力地照射着空旷的街道,寥落的行人,似乎要扔掉变形的影子,匆匆行走。糊涂美人一度要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悄声告诉她,黑夜里也有眼睛,她方始做罢。分手时,糊涂美人特意绕到了一处黑暗的街边儿,我知道她想要干什么,也只能跟着她。糊涂美人站下了,黑暗中,盈盈的眼光看着我,没由我主动,突然她就抱住了我,喊了一声,我可受不住了,热热的嘴唇一下就贴到了我的唇上。一开始,我只能应合着她,糊涂美人的亲吻很饥渴,大有把我吞下去的意思。我抱着她,在酒的刺激下,一会儿也不能自己了。在她亲吻我时,我的手探进了她的怀中,抚摸着她坚挺的乳房,然后一步步将她挤进了墙角,但是,当我的手再往下试探时,糊涂美人似乎一下子惊醒了,拉住我的手,扯着自己的腰带,在我几次想冲破这块防地时,都被她坚决制止了,糊涂美人说:“别这样,守义,在这儿不行。”
“我们再找一块儿地方?”
“以后再说吧。你相信,我一定会将你表姐夫救出来的。”
糊涂美人撂下这句话,幽灵一样消失在了黑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