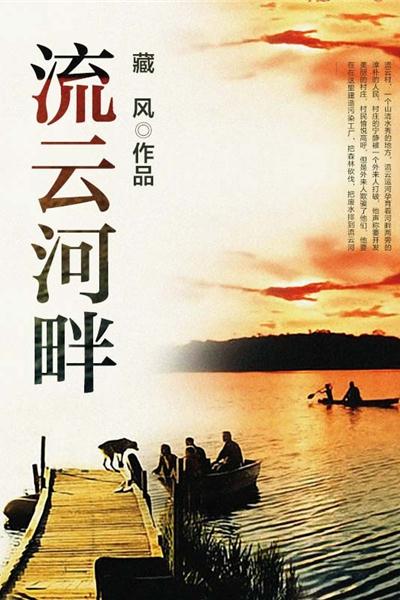牛家坨子的事情,我很少参与,把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除了学习,还有更大的快乐,就是和我那帮朋友的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这帮朋友,都有了一些变化。谭斌越长越胖,也越长越黑,活脱像个小老头儿,我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头儿”;张中原越长越英俊,也越来越傲气,我给他起个绰号叫“王子”……钟玉花和牛淑芬两名女同学,也都长出了自己的特点:钟玉花越长越秀气,就像雨后的一杆绿竹,清翠欲滴;牛淑芬却依然像怒放的大丽花,阳光得从来没有乌云。
我除了在朋友中得到快乐,让我更快乐和自豪的,是我还有了一位好老师,他叫林墨林。
我至今还记得林老师给我的第一印象。
那是我们走进中学的第一节课,同学们坐在教室中,猜测谁来当我们的班主任?这时,一位男老师走进了教室。这是搭眼一看,就给人耳目一新的那种人的感觉。他三十左右岁,穿一身黑色中山装,头发向后梳得一丝不苟,一双眼睛又黑又亮,给人一种特别深遂、特别阳光的感觉。这样的人,只要你看上一眼,就永远都不会忘掉。
林老师走进班级后,看一眼对他同样陌生的学生,点点头,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写下三个字:林墨林。
林老师用浑厚的堂音说:“我姓林,起名墨林。这个名字很宿命,说明我这辈子,都是和墨水打交道的命了。”
同学们一听乐了。
林老师介绍自己别出心裁,讲课也见解独到。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能杀到骨子里,让人思路大开,想一直听下去,可惜每节课刚听到节骨眼上,下课钟就响了。
因为好感,我很愿意接触林老师,沾了当班长的光儿,机会自然很多。我们在一起,除了探讨一些班级问题,有时也讲一些别的,比如我喜欢看课外书,便是林老师主动问起的。那天,我刚要和林老师汇报班级工作,林老师转了话题,问我:“张守义,听说你常看课外书,你都看一些什么书啊?”
老师的口气,不像批评我,让我心里有底了。我带着不无卖弄的口吻,讲了看过的一些书,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呀托尔斯泰的《复活》呀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呀,还有普希金、拜伦、雪莱等一些诗人的作品。
林老师听我看了这些书,眼睛带着赞许的目光,如此,更鼓励了我,向他讲起了哪些书更吸引我。
林老师听后道:“守义,想不到你看过这么多书,你家里一定有很多书了?”
老师这样问,我低下了头,不好意思道:“我家哪有什么书啊,这些书都是牛淑芬爸爸的,牛淑芬借我看的。”
“你是说镇党委副书记牛同?”
此前,我只知道牛淑芬爸爸是当官的,当多大官儿,我一点不知道。
林老师问完这句话,好像感觉自己说话唐突了,解释道:“牛同是个博学多才的人,是个好干部。想不到,你能从他那里看到这些书,真不错。”
星期六下午,我们几个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聚会的场所——学校围墙外的后山坡。所谓山坡并没有山,只是一片高岗儿,知道历史的人说,这里是高丽长城遗址。据说,明时高丽人在此修过长城,和明长城相连。历史早已烟消云散,如今这里被大片的老榆树占满了。知道历史的人又说,这些老榆树,是伪满洲国时栽的,如今也都老了。
秋天了,接连的几场霜,让老榆树的叶子大部分都落光了,只剩下黑色的树身,在遍地黄叶衬托下,展现出一种肃穆的美丽。
所谓聚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不过是同学们找个地儿,在一起闲聊罢了。
我不知道这是我们第几次在这里聚会了。
聚会不久,我们就谈起了各自的老师,听我说林老师课讲得好,张中原接过话说:“守义,你看对了。林墨林可了不得,解放前在日本留过学,据说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呢。别说给咱们讲课,就是给大学讲课也绰绰有余。”
张中原的话让我吃惊不小,原来,林墨林老师还有这样高的学历。
钟玉花提出问题:“林老师这么有水平,又去日本留过学,为什么来我们镇上教书?”
大家把目光投向张中原。
张中原挨个看看我们,略显神秘地说:“林墨林老婆是东排木牟大地主的女儿,叫牟兰。牟兰母亲去世早,她为了照顾父亲,哪也不去。林墨林为了她,这才回国的。我敢说,咱们靠屯街,牟兰长得才叫漂亮呢。”
听了张中原的话,我对林老师的敬重又多了一层:一个男人为爱牺牲一切,确实不容易。那么,林老师的爱人,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呢?我一直很好奇。
又到了周一,同学们坐在教室里,等林老师来上课。林老师没来,李老师来了。李老师叫李萍,她说林老师病了,她来给林老师代课来了。
李萍老师是我们的音乐老师。名曰音乐教师,歌儿唱得实在不音乐,更要命的还有她的长相,用谭斌的话形容,她一张嘴就能吞下脚踏琴。另外,她还有一个朝天鼻子。还用谭斌的话形空,他一天对我说,他从李老师鼻孔,看见了李老师的大脑了。
放学后,钟玉花叫住我,说要去看林老师,我们便叫上谭斌一同去了。
能去林老师家,我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兴奋得让我脸红。
林老师的家,住在靠屯街后岗上,离张中原家不远。
林老师家的房子,也是青砖灰瓦的,但没有牛淑芬家的房子大,房顶上生满了杂草,看上去有些荒凉。不过,大门比较别致,灰黑的粗糙木头大门,钉了很多铜锔子,显得特别牢固。后来才知道,那是牟兰家里留下的遗物。钟玉花瞅我看着大门,以为我不好意思敲门,走上前,落落大方地敲了几下,不久,大门里面有了动静,大门被拉开了。
大门打开的那一刻,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道彩虹。我敢说,什么词儿用在眼前的发现都不为过,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美艳绝伦……一年前,我看过法国作家莫伯桑写的《羊脂球》,用羊脂来形容女人的圆润、通透、肤如凝脂,我因此会联想到眼前的发现。总之,长这么大,我从来还没看见过这样漂亮的女人,白嫩、明眸、皓齿、鼻梁挺直……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站在仙女面前,好像多看一眼,都是对仙女的亵渎。
不用说,这就是林老师的爱人,我的师母牟兰了。
师母未语先笑,眼睛里也同样涌出笑意,轻声问:“你们找谁呀?”一个人漂亮,连声音都好听。
我当时太过于激动,或者紧张,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钟玉花抢着说:“我们是林老师的学生,听说林老师病了,我们来看看。”
师母再次笑笑,闪到一边儿,将我们让进屋中。经过她身边时,我鼻子中闻到了一股奇异的香味儿,就像我家大河套里的铃兰,清新、雅洁,让人魂牵梦萦。
林老师家共三间房,一进门是灶台,收拾得干净整洁,中间是客厅和书房,里间是卧室。牟兰将我们让进客厅,倒水、拿糖果,尽一个女主人的客套。
师母忙着时,林老师从卧室中走了出来。
林老师看不出有什么病,脸色很好。他瞅一眼牟兰,满眼都是柔情,然后把目光投向我们,问道:“哦,是你们来了,班级有事了?”
“班级没有事儿,李萍老师说你病了,张守义说想看看你,我们就来了。”钟玉花越来越会说话了,抢了你的话,还把功劳推在你身上,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外交本领。
林老师笑着说:“没事了,明天就可以上课了。”
林老师招呼我们坐下,他和师母坐在一起,这才想到给我们介绍“这是我爱人,牟兰,回族人。”说完,拉住师母的手,对我们几个学生就在眼前毫不在意,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我心想,难怪师母这样漂亮,这样白净呢,全身散发出原野的气息。我当时一定傻傻的,对师母想看又不敢看,不敢看又忍不住好奇,眼睛的余光全在师母身上了。
师母误以为我在看她身后的书柜,笑着说:“这些书,都是你们老师的。他宁可丢掉我,也不会丢掉这些书。”
师母如此说,林老师微微一笑,我发现,他将师母的手握得更紧了。林老师要大师母四五岁,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结合到一起的。但看他们坐在一起,感觉更为般配。
钟玉花很会说话,道:“林老师才不会呢,他就是丢下一座金山,也不会丢下您的。男人要丢掉一位这样漂亮的爱人,一定是个傻瓜蛋子。”
钟玉花的话,让大家开怀大笑。
自从认识了林老师家的大门,这里又成了我的另一座精神宝库。除了林老师那些书吸引我,还有师母牟兰。一位成熟的女人,对我有如此的吸引力,我不知道,我是出于怎样一种心理?总之,能看上一眼师母,我心里便满满的,特别充实。
这也许就是爱了吧。但我并不敢往深里想,她是我尊敬的老师的爱人,好像多想一下,都是乱伦,都是亵渎,但是,越控制自己,往往想得越多,尤其到了晚上,仰望着黑暗的天棚,听着夜风走过树梢的声音,神思往往飞得很远,所有的神思,往往都和师母有关,但模糊在脑海里的形像,却是夕阳下远去的背影,充满了无尽忧伤。
有时,我也会将师母和牛淑芬和钟玉花相比。
牛淑芬大气、妖娆,是太阳刚刚脱离雾霭的灿烂,辉耀着原野的清风;钟玉花清秀、恬美,是飘在黎明中的白云,给人清幽、恬淡的感觉;师母温婉、清新,只属于幽谷的黎明,属于花叶上的露珠,通透得没有一粒灰尘。
当然,这些想法,只属于一个少年朦胧的爱恋,很难再找出深一层的意义了。
对比完几个女人,我又开始对比牛同的书和林老师的书。
牛同的书和林老师的书,数量差不多。牛同的书,更庞杂一些,林老师的书,更专业一些。林老师是读历史的,就像牛同当干部离不开马列一样,他也离不开二十五史。过去,听人总讲二十四史,到了林老师这里,他又给补上一史。他说,中国过去说二十四史,遗漏了一部最重要的史书——《金史》。《金史》是大金国倒台半个世纪后,大金的敌人大元编的。这部史书,最为客观。其他史书,讲到东北,大多带有偏见。要研究东北历史,一定要读《金史》。林老师如此说,因为他便是研究女真史的。林老师说,他回国,就是想在女真故土上研究女真史。这和张中原说的老师为了爱情回国,实在有些出入,但是,一个男人如果没有爱情,光为事业而活,又有些苍白。
此后一段时间,我成了一个书痴,去林老师家借书还书,去牛同家借书还书,每一本书,都为我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感受到一个新的世界,甚至,好像看到了那个遥远的世界,正在向我频频招手,引导着我一步步向前走去……当然,除了读书外,每次借书还书,还能看到牛淑芬和师母,这是我另一种隐秘的动力,或者说,因为她俩,我更爱读书了。
少年的思想,总是纠缠不清。
但是,社会的变化,却没能让我将这个梦继续做下去。
时间到了1957年7月份,国家开始了XX运动,号召广大群众和知识分子给XX提意见,还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口号。就连我们学校,校长王大胖子也一改往日作风,请同学和老师提意见。同学倒是提出一些意见,无非是食堂饭菜不好,总给领导开小灶,因为当时驻校同学伙食费是平摊的。
王大胖子装模作样地记着,又开始鼓励教师提意见,主要是给X挑毛病。
教师们无人发言。
王大胖子点名了,点的第一个人就是林老师,说道:“林墨林老师,你是咱们学校学历最高,也是学问最高的人,还是你说说吧。”
“我没啥说的。”
一些老师起哄:“让你说你就说吧,客气啥?”
林老师强推不过,走向主席台,说道:“其实(此处删去280字)”
林老师讲完这些,看到大家惊愕的表情,打住了话题,补充道:“我今天就讲这些,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大家谁都没说一句话,王大胖子只是低头记着,好像不知道林老师讲完了。
林老师走下了主席台。
王大胖子抬起头来,皮笑肉不笑地说:“林老师讲得好,不管对与错,我们X都欢迎大家提出批评意见。这就叫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说完,带头鼓起掌来。
大家见校长鼓掌,也都跟着鼓起掌来。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事情过去两个多月,当大家渐渐遗忘了这件事时,学校里突然来了两个民警,将正在上课的林老师抓走了。
林老师突然被抓,同学们不知道老师犯了什么罪?议论纷纷。我没有参与议论,一口气跑到林老师家,要将这个消息告诉师母。
师母刚洗完头,一头秀发垂在脑后,正用干毛巾擦拭着,看我气喘嘘嘘、面色苍白地闯进屋中,很惊讶,满眼都是疑问,问我:“怎么了,守义?”
我喘了半天,这才将林老师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师母。
师母听后,头发不擦了,手和头发一起垂了下来,她倚在书柜旁,整个人儿傻了一样。
我安慰她:“也可能没什么事儿,他们就是找他谈一些事儿,要抓人,怎么能不给人带手铐呢。”
师母一声不吭。
我开始劝师母,说:“你千万不要着急上火。事情发生了,我们再想些办法。我同学牛淑芬张中原,他们的父亲都在镇里做事儿,我托他们打听一下。”
师母这才缓过气来,说道:“谢谢你,守义。看来,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现在,全国都在抓XX,我估计,他们是要抓他XX。”
师母的话,马上就得到了证实。这天中午,学校通知召开紧急大会,让同学们全部参加。
刚刚被抓走的林老师又被押回来了,还跟来了很多县里镇里的领导,他们在主席台上一落座,批斗会就开始了。
首先发言的是校长王大胖子,他很激动,脸红红的,拿出发言稿,看来早有准备……(此处删去300字)王大胖子激动万分地讲这些时,押在台上的林老师一声不吭。
我在下面气不过,很想喊上几句,谭斌扯下我的衣角,可能看出了我面红耳赤。朋友交长了,每一个微小的习惯都清楚。谭斌说:“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你没看,王大胖子后边那一堆人么?”
我心里刀扎般的难受。
林老师在我们学校批判完后,齐家公社来人了,将林老师押到齐家公社,继续批判。
林老师被押走后,我们这群朋友,来到我们的聚会地点。
冬天了,没有雪,大地冻得干巴巴的,那棵谭斌经常攀爬的老榆树,沉重得像块铁,面色冷峻地注视着冷冰的大地。
我开门见山,气愤地说:“(此处删去120字)”
着急,激动,我一口气讲了一大堆。
牛淑芬比较冷静,说道:“守义,你的话我信。可是我们还太小,说话他们会信么?”
张中原说:“我父亲说,抓XX是有指标的。一个地方不抓几个,上边通不过。王大胖子抓林老师,就是为了完成指标。”
我说道:“那我们就更要反了,去揭露王大胖子的罪行。我们不能因为什么指标,就毁了一个人。同学们,我们要组织起来(此处删去70字。”
我被自己的正义感染了,钟玉花一句话,却让我冷静下来,她说:“事情发生了,急也没用。林老师一个男子汉,怎么都能挺过来。就是不知道师母怎么样了?土改时她父亲被打死,现在丈夫又被抓,她能挺住吗?我们还是去看看她吧,兴许,她还能拿个主意。”
牛淑芬听后点点头,说道:“玉花说得对,我们先去看师母,再决定怎么做。”
牛淑芬都这样说了,我也只能点头,和大家去了林老师家。
师母没有想象的那样憔悴,清锅冷灶的,再也看不到她温婉的笑容了。钟玉花叽叽喳喳,一会儿就将我的想法讲了出来。师母听后道:“你们是学生,不要冲动,怎么办?还是先听听你们老师的意见。”
我说道:“林老师被他们抓起来了,我们上哪听去?”
师母说:“他们通知我了,晚上林老师押回镇上,让我去送饭。到时,我们听林老师怎么说。”
师母如此说,我也只能压下心里的冲动。
第二天傍晚放学,我刚走出校门,就见墙拐角站着一个女人。女人穿件苏式黄色棉衣,围着头巾,头巾围得很严,除了眼睛,什么都没露。我感觉那身影很熟悉,果然,我刚走近,就听一个亲切的声音喊我:“守义,过来一下。”
是师母。
师母带我拐过墙角,又走了一段距离,在街旁一块不大的玉米地旁停下了。玉米掰走了,玉米秸没割,枯黄的玉米叶子,在冷风中,发出哗哗啦啦的叫寒声,让人联想到灵幡。师母回过头来,盯着我的眼睛说:“这么冷的天,怎么连个帽子都不戴。”说完,解下围巾,就要往我头上围。我赶紧拒绝伸手来挡,没想到,一下子碰到了师母光滑的手,那一刻,我心里过电一样颤抖了一下。师母还将我当成孩子,我感觉自己早就是大人了。
师母没再坚持,说道:“过两天,我给你织一顶帽子。”
师母不知道是激动,还是因为在学校前怕人看见,她白嫩的脸上微微泛红,告诉我:“我看到你们老师了,也将你的想法告诉了他。林老师让我转告你,千万不要闹,那样,会让他增加罪行。再一个,你们老师说,批斗一段时间就过去了。他和国家不是敌我矛盾。上面的意思是,只要他能和上面统一了思想认识,就放了他。”
听了师母的话,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了。
师母说完,叮嘱我道:“千万记住了,不能带学生去闹。”说完,转过话题:“看你的耳朵都冻红了。”说着,伸出两只手,一下捂在我双耳上。师母的手又暖又滑,霎那间,温暖电流一样传遍我全身。我的个子高出师母半个头,她还将我当成一个孩子,那片刻的温馨,足以温暖我一辈子。
师母感觉将我的双耳焐暖了,摘下围巾,强行围在我头上,告诉我,她家近,我家远,不要冻着了。
那是一条赭石色的围巾,像秋天的原野,充满了成熟的味道,整个晚上,我都将围巾放在枕旁,鼻子中充满着清新、甘甜,让人的神思飘到了丰收的原野。
第二天,我去给师母送围巾时,林老师已经回到了家中。林老师脸颊红肿,眼眉裂开一道口子,已经结痂,看到我,眼神亮了一下。
看到老师这样样子,我心里十分痛楚,嗫嚅道:“老师,他们……”
“没事儿,打几下,伤不了筋骨。”
“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你?你啥时(删去20字)。”
“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哈哈……”
师母嗔怪他道:“都将你打成这样了,还有心思笑?”
林老师道:“人到啥时都要看得开,再大的风暴,也有停下来的时候。对了,守义,听牟兰说了,你要带学生去闹?你还小,不知道这里边的凶险,以后千万不要冲动。”
“那你以后还给我们上课吗?”
林老师愣了一下,情绪有些低落,道:“这个……恐怕就难了。王校长通知我了,明天上学校后勤报到,去种菜。”
“这个季节种什么菜?”
“王校长是不会让我消停的。”
离开林老师家时,师母叫住我,说道:“我答应给你织顶帽子,一时来不及了,这个滑冰帽是你老师的,你先戴着。”
师母说完,不容我拒绝,将一顶蓝色的滑冰帽戴在我头上。
王大胖子果然没有让林老师消停,第二天,就安排林老师去了学校的菜地。冬天自然不能种菜,但可以为做种菜准备。林老师和学校几名校工拉着平板车,开始满镇找厕所,干上了掏大粪的工作。
自此,上学、放学,常会看到林老师拉着粪车的身影。
那是一幅凄怆的画面:灰黑的土路上,林老师穿着同样灰黑的衣服,戴着棉帽子,围着口罩,步履蹒跚地拉着散发着臭味儿的大粪车,在寒风撕扯下,是那样孤单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