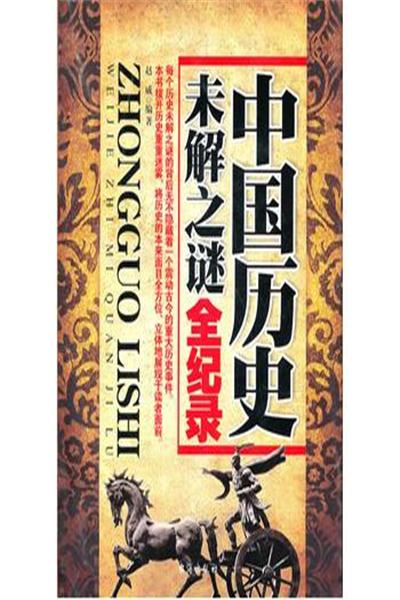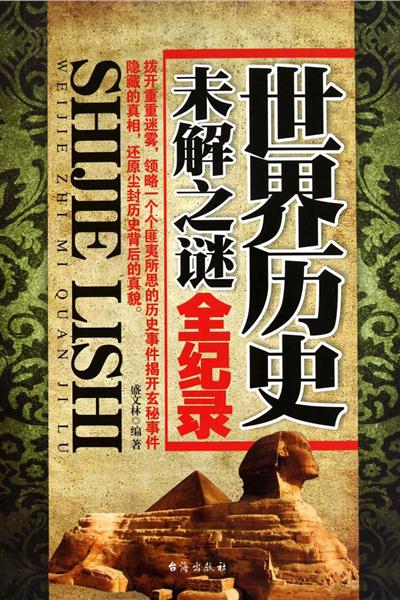第15章
但是,学术界也有人不同意上述观点。十月革命后,苏联有的学者写道:“俄国中国学家的骨干由北京俄国布道团成员——东正教士组成。他们在传布基督教的幌子下执行着外交职能,他们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殖民政策的积极传导人。”我国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比丘林在北京活动期间搜集情报,探取中国内政的机密,窃取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资料。他绘制了《北京城廓图》。离京返俄时,他带走的图籍、手稿重达1.4万磅,分装15头骆驼驮运。这是“侵略行径”。他在恰克图创办华语学校,积极训练一批从事对华商业扩张的骨干。因此,是一个“侵略分子”。三,是“俄国中国学之父”,还是“学为沙皇所用”的“神棍”?过去苏联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比丘林为俄国有关中国史的广泛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他的历史著作阐述了中国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的许多问题,论述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中国和中亚各族人民的历史。就他研究问题的广博、规模和科学研究作品与译文所使用的中文史料的范围来说,比丘林都远远地超过西欧同时代人。他实际上是俄国的中国学的奠基人,是“俄国中国学之父”(布纳科夫语)。近年来,我国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比丘林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兴趣,盛赞中国高度完善的史学体系和神奇发达的中医、中药,并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丰富性和科学性表示惊叹不已。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最主要的研究领域,不止一次地抨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种种歪曲。他留下一百多部(篇)有关中国的专著、译著和论文,此外,还有一万多页未发表的手稿。他对中国的介绍和中国学研究的领域之广、著述之丰、阐释之深,都远远超过号称俄国第一代中国学家的罗索欣、列昂节夫等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俄国的中国学是与比丘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学术界也有人持与此相反的见解。例如,前苏联学术界有人认为,包括比丘林的“中国学”在内的俄国“旧中国学”是作为俄国专制制度政策的思想武器而发展起来的,沙俄在东方的推进在旧中国学中反映出来并找到辩护的理由。我国学术界有人指出,比丘林的“中国学”以中国边疆地区作为研究的重点,完全适应沙皇政府对中国有增无减的领土野心。俄国中国学发展的“比丘林时期”是“学为沙皇所用”的新阶段,比丘林作为俄国东正教的“神棍”,在“学为沙皇所用”的道路上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比丘林到底是什么人?他的中国研究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巴枯宁为什么写《忏悔书》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年)是俄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俄国民粹派运动的领袖。他一生思想复杂,经历坎坷,但他最能引起争议的活动恐怕还是他在被捕后撰写《忏悔书》的事件了。
巴枯宁出身俄国封建贵族家庭,少年时接受了父亲的自由主义教育。1835年进入俄国著名学府——莫斯科大学学习,积极加入思想激进的斯坦凯维奇哲学小组,结识了后来的民主革命家赫尔岑、奥加辽夫、别林斯基等人。他厌倦俄国社会的沉闷和窒息,向往自由的空气和激情的生活。1840年秋,他离开俄国,来到当时欧洲资产阶级思想最活跃的德国求学,从此他的政治思想和倾向发生了巨变。他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所吸引,成为民主主义的狂热信徒。1842年10月,巴枯宁在其第一篇政治论文《论德国的反动)中向专制制度发出了公开挑战,他声言:“难道你们没有在革命建立起来的自由庙宇的山墙上看到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神秘和可怕的字眼吗?难道你们不知道和没有感觉到,这些字眼意味着现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彻底消灭吗?”此文标志着他已彻底与贵族阶级决裂,同时也表明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萌芽。此后,巴枯宁放弃了做大学教授的梦想,走上了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道路。巴枯宁在自己著作中,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虚伪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他揭露在专制制度统治下的俄国,“既没有自由,也没有对人的尊严的尊重”,痛斥沙皇是“鞭子沙皇、盗贼沙皇和害人者沙皇”,呼吁俄国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当时,沙皇政府以一万卢布悬赏巴枯宁的头颅。他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时指出:“不论它们的色彩和名称如何,实质上只能有一个目的,维持资产阶级统治,而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对无产阶级的奴役”。应该说,巴枯宁激进的政治主张和言论在启发各国工人的斗争意识,揭露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号召和发动群众革命方面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