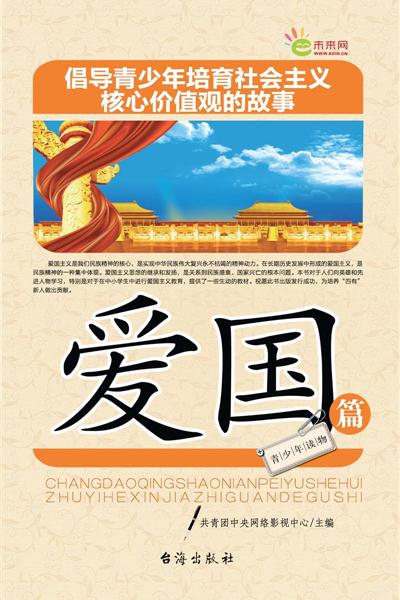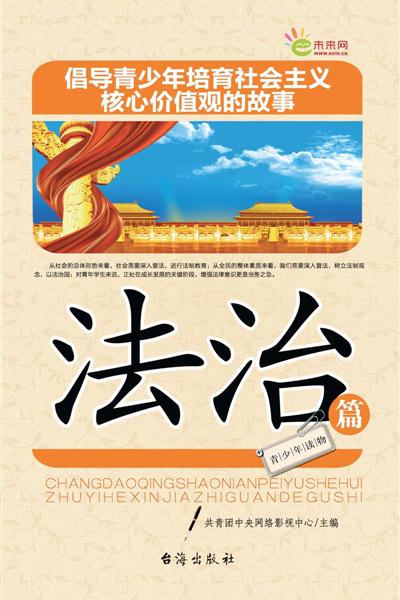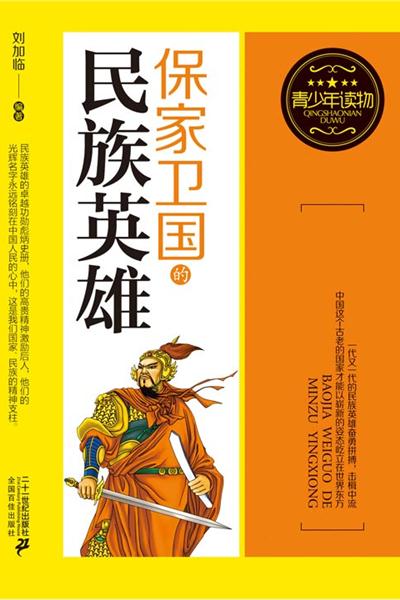简介
李贽(1527—1602),中国明代后期思想家。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原姓林,名载贽,汉族,先世祖受所娶胡妇影响皈依过回教。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举后,改姓李,嘉靖三十五年为避穆宗载垕(同“厚”)讳,取名贽。其家是世代巨商,至祖父辈家境渐衰。他曾接触过王守仁学说,并研究佛学。归隐后,主要从事研究、讲学和著述。
1588年和1590年先后有初潭集和焚书问世,书中尖锐地揭露了道学家的虚伪和自私,受到耿定向等人的攻击和迫害。1599年藏书问世,受到进一步迫害。1602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下狱。李贽76岁在狱中受到严重迫害,不堪忍受,于是请一位剃头师傅为他剃头,其间乘人不备夺过剃刀自杀身亡。他的著作,曾多次遭到禁止和焚毁,但仍继续流传于世。
生平
李贽生活的时代
李贽生活在明代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这时,兴盛的明王朝已经走向了下坡路,中国的封建社会也进入了后期阶段,正是一个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多事之秋。
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皇族和大地主手中。弘治(明孝宗年号)年间,皇庄、官庄已有三百多处,占地四万五千余顷。嘉靖(明世宗年号)、隆庆(明穆宗年号)间这种趋势继续增长,万历(明神宗年号)时期,更有了恶性发展。明史·食货志记载,明神宗时,“福王分封,插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官僚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也相当惊人。大官僚徐阶一家就占有土地二十四万亩,至于拥有上万亩土地的地主则到处都有,而多数农民却无立锥之地。顾炎武日知录说:“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土地的高度集中,形成了广大农民与大地主之间的尖锐矛盾。
李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以剥削雇佣劳动为特点的手工工场。仅苏州一地,在这种手工工场中劳动的工人就有数千之多。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要求打破封建制度的束缚,并且很快就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公元1601年苏州发生的罢工抗税斗争就是其中的一例。
明王朝的统治,以高度的中央集权为特点,法令严酷,特务横行。高踞在庞大官僚机器之上的朝廷,政治昏庸,生活腐化。他们大兴土木,到处搜罗珍奇玩好,弄得府库空虚,帑藏匮竭。于是他们挖空心思,箕敛财贿,巧立名目,增加赋税,以致人民负担空前沉重。再加上连年外患,倭寇骚扰,给社会生产带来很大破坏,造成怨声载道、流民遍野的严重情况。
社会矛盾的加剧,使统治者不得不强化思想统治。早在宋代,就出现了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代表的道学。道学家把封建伦理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人民俯首帖耳当奴隶。到了明代,由于统治者的提倡,道学流毒更广。不少并无真才实学的人,只知空讲义理,猎取名利,对于国家大事束手无策;有的人甚至口称仁义,行同狗彘,造成层出不穷的政治丑闻。嘉靖年间,奸相严嵩掌权,朝臣三十余人自愿充当义子。这种日益颓下的士风,也是封建王朝趋向没落的一个重要标志。
李贽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他去世时,距明朝灭亡只有四十二年,距明末全国农民大起义只有二十多年。他行经南北十余省,对社会情况有不少了解。作为一个不受儒家传统思想束缚、而又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不提出自己的主张。
李贽的生平和著作
李贽,号温陵居士,又号宏甫、龙湖叟,福建省泉州晋江人。泉州早在宋代就设立了市舶司,一直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他的祖宗几代都从事航海活动,父亲可能是一个教书先生,家境并不富裕。李贽生于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六年(1527),死于明神宗(朱翊钧)万历三十年(1602),活了七十六岁。他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青年时期:从嘉靖六年至三十四年(1527—1555)。
李贽出生不久,母亲便去世了。因此,他从童年便学会了料理自己的生活。七岁随父亲读书,善于独立思考,能够提出不同的见解。十二岁时,写了老农老圃论,对论语·子路篇的樊迟请学稼章做出了新的解释,受到人们称赞。
李贽从二十岁起,就离开家乡出外谋生。艰苦的生活磨炼,养成了他倔强的性格。他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李贽蜡像
李贽本是讨厌科举的,所以对朱熹的四书集注也读不下去。但是,环境偏要逼他去干不愿干的事情,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苦恼。他一方面不得不像一般应考举子那样,背诵一些时行的八股文,以便应付考官,并在二十六岁考中了举人;另一方面,又深感这种做法的无聊,曾讽嘲地说:“此直戏耳!……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因此,他不愿再到京城参加会试,认为只要有个糊口的手段,能有机会研究学问,也就够了。
宦游时期:嘉靖三十五年至万历八年(1556—1580)。
李贽第一次做官是到河南辉县当教谕。在辉县过了五年,嘉靖三十九年(1560)升为南京国子监博士。到职后数月,便因父亲去世,回家守制。李贽此次回家,正逢倭寇肆虐,他在路上,昼伏夜行,回家后,又登城守卫。由于战争关系,粮食短缺,全家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丧服期满,他便携带家眷到了北京。
嘉靖四十三年(1564),李贽就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但不久,他的祖父又死了,他便将妻子黄氏和三个女儿安排到辉县居住,自己回乡奔丧。不料,这年河南闹灾荒,二女、三女相继饿死。李贽在家住了三年,回到辉县后,与妻子对坐灯下,共诉往事,不觉凄然泪下。
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四年(1566—1570),李贽在北京补礼部司务,并开始接触和研究王阳明的学说。
隆庆四年至万历五年(1570—1577),李贽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在这里,他曾拜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开始接受了泰州学派的影响。
万历五年(1577),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由于在长期的宦游生活中,亲身感受到社会矛盾的尖锐,所以他针对“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的情况,主张宽以驭下,向上司提出了对于“边方杂夷”,要宽法缓征的建议,不但未被采纳,反而因此触犯了上级。
李贽为官二十余年,经常触犯权势者,而同那些一味坚持儒家教条的人,又格格不入。他说:“大概读书食禄之家,意见皆同,以余所见质之,不以为狂,则以为可杀也。”所以他厌倦官场生活。李贽在姚安知府任内,政绩不错,巡按云南的御史刘维要把他的政绩上报朝廷,以便加恩晋级。但他坚决反对,认为那样做是“贪官”、“贪荣”、“钓名”,便于任满前两个月提出辞职。由于他为官清廉,临走时,“囊中仅图书数卷,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
万历八年(1580),李贽离开云南,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宦游生涯。
隐居著述时期:万历九年至三十年(1581—1602)。
李贽于万历九年(1581)来到黄安,住在好友耿定理那里,专心读书著述。但不久,耿定理去世,他与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意见冲突,无法共处。便于万历十三年(1585)将家眷送回原籍,自己搬到离麻城三十里的龙湖芝佛院居住,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生活。
龙湖在群山环抱之中,与外界来往很少,环境是幽静的。但是,李贽的心情却无法平静,他把多年积压在胸中的愤懑,都在自己的一部部著作中倾泄出来。他厌恶那些道学气味很浓的俗儒,说同这些人“但一交手,即令其远坐,嫌其臭味”。对于欺世盗名的假道学,更是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万历十八年(1590),他的焚书出版了,其中收录了揭露道学家耿定向的七封信。李贽以犀利的笔锋戳痛了伪君子的伤疤,引起了他们的疯狂反扑。于是,本来宁静的龙湖不宁静了,碧绿的深潭中掀起了波涛。耿定向鼓动他的徒弟写了焚书辨,且编造谣言,诬蔑李贽“引诱良家女子”,“左道惑众”,在李贽游武昌黄鹤楼时,耿定向雇用流氓将其赶走。他们还借助于担任巡道御史的史某的权势,扬言要将李贽驱逐出境,递解回籍。面对这些迫害,李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说:“我若告饶,便不成李卓老矣!……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又说:“自量心上无邪,身上无非,形上无垢,影上无尘,古称‘不愧’、‘不怍’,我实当之。是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日与世交战而不败者,正兵在我故也。正兵法度森严,无隙可乘,谁敢邀堂堂而击正正,以取灭亡之祸欤。”
万历二十四年(1596),李贽去山西等地讲学。两年后,再次来到南京。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南京出版了另一部重要著作藏书。
李贽故居
当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贽回到龙湖的时候,麻城的反动势力正在勾结地方官吏策划一次对他的更大迫害。由于李贽曾在万历十六年(1588)落发出家,所以迫害者便打出“逐游僧,毁淫寺”、“维持风化”的旗号,拆毁了芝佛院,烧掉了李贽准备安放自己遗体的塔,来势异常凶猛。李贽由于事先被人接走,才免于难。于是,这位七十四岁的老人,不得不再次经受颠簸之苦,忍痛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龙湖,前往河北通州去依附好友马经纶了。
李贽在通州住了一年多,身体一直虚弱多病。为此,他曾经写下了遗嘱。但是,反动势力并没因其已到了风烛残年而停止对他的迫害。京城的一个官僚张问达居然上疏劾奏李贽,说他刊刻焚书、藏书,惑乱人心,随意褒贬古人;在麻城勾引士人妻女,挟妓女白昼同浴,败坏世风。若不赶快处置,李贽势必要把北京变成第二个麻城。这些人的用心是极其恶毒的,而其手段又是十分卑鄙的。为了置李贽于死地,不仅无中生有,构词诬陷,还硬说七十老翁挟妓纵淫,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明神宗朱翊钧看到奏疏,立即下令逮捕李贽,焚毁他的著作。这时,李贽已经病卧不起,他躺在门板上被抬进监狱,一路昏迷,粒米不进。到监狱后,又躺在台阶上接受审问,但态度仍然十分倔强,使审问官束手无策。李贽在狱中,决心以死做最后的反抗,曾作诗道:
四大分离象马奔,求生求死向何门?
杨花飞入囚人眼,始觉冥司亦有春。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待何时?愿早一命归黄泉。
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十五日,李贽用剃刀自刎,第二天气绝自死,时年七十六岁。这位战斗了一生的反道学战士,最后又用鲜血写下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控诉状:
李贽一生著述很多,最重要的是岱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
焚书六卷,是李贽的诗文集,收录了他的书信、杂著、史论、诗歌等,最早刊刻于万历十八年(1590)。作者在自序中说:“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这就是命名焚书的由来。续焚书五卷,是李贽死后由他的学生编成的,最早出版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内容大致与焚书相同。
藏书六十卷,续藏书二十七卷,都是李贽后期评述历史人物的著作。藏书主要取材于历代正史,载录了自先秦至元末的历史人物约八百名;续藏书取材于明代的人物传记和文集,载录了神宗以前的明代人物约四百名。李贽按照自己的观点把这些历史人物加以分类,对一些人物事件和言论写了专论或评语,富于批判精神,表达了他进步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李贽自知此书“与世不相入”,说:“吾姑书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藏书·梅国桢序)这是取名藏书的苦心。藏书最早刻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续藏书最早刻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
以上四种书是研究李贽思想的主要资料。解放后,经中华书局校订、标点,重新出版。解放后重版的李贽著作还有史纲评要三十三卷,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另外,李贽的著作还有初潭集、李氏丛书、李氏六书、易因等多种,因流传的版本很少,不易见到。
李贽对封建礼教的批判
李贽对于封建礼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说:“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他的异端思想,归纳起来就是:反权威、反传统、反专制。
李贽墓
李贽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人的德性也是“今日新也,明日新也,后日又新也”。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因此,他反对机械地学习古人,认为那是“效颦学步”,更反对把封建圣人孔子的话当作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把孔的是非当作今人的是非。他说:“前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祖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他告诫藏书的读者:“览则一任诸君览观,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罚赏也。”对那种“亦步亦趋,舍孔子无足法者”的道学家,他是十分鄙视的。在答耿中丞书中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李贽还说,尊孔的人实际上并不知道孔子有什么可尊敬的,不过如“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犹如“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孔子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权威,李贽不仅否定他的权威地位,而且把尊崇这个权威的人都比作无知的矮子,甚至比作吠形吠声的狗,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李贽不仅敢于亵渎圣贤,而且还毫不留情地贬低六经。他认为,这些书“大半非圣人之言”,“纵出自圣人,要亦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
六经一向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的经典,李贽这样无情地攻击它,正是在摇撼着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
李贽还通过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表现了勇敢的反传统精神,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伦理道德。比如,他写的藏书,就是抛弃了传统看法,而以自己的是非标准评价人物的。他说:“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唾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
君臣关系是封建伦理的核心问题。李贽反对以忠君作为评价人物的道德标准,也不同意君主臣仆的传统观点。他认为君臣关系应该像朋友一样:“君臣以义交也,士为知己死。”如果君主昏庸,那么臣子就要强谏:“臣之强,强于主之庸耳。苟不强,则不免为舐痔之臣所谗,而为弱人所食啖矣。”又认为人之贵贱取决于德行,而不在于政治地位的高低:“盖天唯德为至贵,德在我矣,时位恶能限之?……使庶入而有君德,亦自然为利见之大入,使上焉者而无德,则虽位居九五,其谁利见之哉?”李贽这些重民轻君、君民平等的见解,是对于封建的君臣伦理关系的否定,也是对于明代的那些独断专行而又昏庸腐化的君主的有力鞭挞。
在妇女问题上,李贽批判了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表现了十分卓越的见解。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认为男女在智慧上是没有区别的,有些妇女知识不够,主要是因为封建礼教的束缚,使她们不能外出学习的缘故。李贽赞成男女自由婚嫁,在批评红拂记第十出侠女私奔的批语中说:“这是千古以来第一个嫁法!即此一事,便是图王定伯手段,岂可以淫奔目之。”他还主张寡妇可以再嫁,对于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恋爱评论说:“相如,卓氏之梁鸿也。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呼!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归凤求凰,安可诬也!”在四百年前的中国,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还统治着人们头脑的时候,李贽这些大胆的议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李贽的书
为了反对强加给人们的封建礼教,李贽还提出了“童心说”。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为什么会失去童心呢?就是因为“道理闻见日以益多”,而“道理闻见皆自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换句话说,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蒙蔽了人的童心。因此,他要求摆脱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要人拿出真心去客观地认识社会问题。李贽的“童心说”和王阳明的“良知说”,都强调人人生知,在哲学上表现为唯心主义,但二者的着眼点和社会效果却大不相同。“良知说”把封建伦理说成是人之本性,要人们服从封建道德的束缚,而“童心说”则认为恰恰是封建的伦理道德玷污了人的纯洁的本性,具有一定的反封建传统的进步意义。
李贽在现实生活中,正是按照“童心说”的基本思想去实行的。他“平生不爱属人管”,强调个人自由,力求摆脱封建桎梏的束缚。因此,李贽不管到哪里做官,都与上司相抵触。从云南辞官后,他不回原籍,而要寄居外地,因为“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其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宁飘流四外,不归家也。”他自称“流寓客子”,“兼书四字,而后作客之意与不属管束之情畅然明白”。据他自己说,他在龙湖落发出家,也是为此:“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管束,况别省之人哉!”李贽的隐居和出家,是有着消极、避世色彩的,但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反抗封建专制的一种手段。他是出身于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阶级的限制使他不可能投身到人民斗争的洪流中去,因而只能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的反抗。李贽声称:他的出家,一不是厌世,逃向虚无;二不是怀才不遇,待价而沽;而是像陶渊明一样,不肯向权贵折腰,不肯与世俗妥协的表现。所以他虽出家,仍然“不持斋素而事宰杀,不处山林而游朝市,不潜心内典而著述外书”。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依靠这种个人的反抗,当然不可能争得自由,但李贽反对封建束缚,要求个人自由的思想,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他那种不畏强权,反抗旧传统、旧势力的精神,也给后人以极大的鼓舞。
李贽的反道学思想
李贽与封建道学家斗争的一生中,对道学家的揭露和批判,更是值得我们认真回味的。李贽首先批判了反动的“道统论”。“道统论”是道学家抬高自己、吓唬别人的一张老虎皮。他们说,“道统”由尧舜传到孔子,再传到孟子,以后就中断了。而程朱学派则是直接继承了孟子的“道统”。道学家用这种唯心主义的手法,把自己说成是尧舜孔圣的正脉,封建制度的合法辩护人。对此,李贽批评说:“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则水无不在地,人无不载遭也审矣。……彼谓轲之死不得其传者,真大谬也。”他认为,既然“人无不载道”,那么,道学家所说的,孟轲以后,道统中断,直到宋朝,才有“濂洛关闽接孟氏之传”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道不能离开人的生活而存在,“人无不载道”的提法,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它戳穿了神秘的“道统论”谎言,剥掉了道学家戴在自己头上的光环。
李贽同时还批判了道学家的“理能生气”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根本不是道学家所说的在天地之先的“太极”,或凌驾于气之上的“理”。最初只是天地,只是阴阳二气的对立。因此,李贽对于世界本原的解释是唯物的,他以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为武器,否定了“理”和“太极”,动摇了道学的哲学基础,在思想史上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李贽更进一步对道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口号给予了严厉批驳。他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食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同者耳。”又说:“夫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自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食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这就是说:第一,物质的需要是人的本能,是任何人包括圣人和主张“灭人欲”的道学家在内的人都不能逃避的;第二,离开了人们的物质需要,离开了穿衣吃饭,没有别的抽象的理。李贽用这种朴实的道理,揭穿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口号的虚伪性。
与道学家相反,李贽既不讳言人的物质欲望,也不讳言人的私心,反而认为私心是人生而有之的:“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
把自私说成是人的天性,这正是市民意识的反映。用利己主义的冰水去掩没空泛的道德说教,用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去代替为伦理关系掩盖着的封建特权,这在历史上曾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因此,李贽不仅承认自私是人的天性,而且还进一步要求社会顺应这种天性,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余地。在李贽看来,顺其私心,能坐致太平;违其私心,则天下大乱。这样,李贽的治世之道与道学家完全相对立。这表现了他是站在市民立场上,提出摆脱封建束缚和发展自由竞争的愿望。
李贽还强调发展生产,崇尚功利,而反对道学的空谈义理无所事事。他说:“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吾遭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又何时而可明也?”他主张开发“山海之藏”,“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对于战国时期变法图强的人物如李俚、吴起,李贽都倍加赞扬。相反,他对于在政治上毫无建树的道学家则十分反感。他批评朱熹说:“吾意先生必有奇谋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于屈辱。”但是,并没有见到朱熹拿出“嘉谋嘉猷入告”。他嘲笑道学家们“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但当国家一旦有事,他们便“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外患频仍,尤其是倭寇入侵,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损失。但是统治者束手无策,坐令东南糜烂数十年。李贽亲身经历战乱之苦,心情十分沉重,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与道学的冥悟空谈有密切关系。他写诗说:“当时王、谢成何事?只好清谈对酒垆。”对于那些清谈误国的道学家,他怎能不嫉之如仇呢?
正因如此,李贽怀着极大的义愤,揭露了道学家欺世盗名的丑恶嘴脸。他指出,道学家都是一些无才无学的人,他们讲道学,不过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无学硬要装作有学,内心卑鄙,嘴上说的仁义道德、正心诚意,说得好听,所以道学家在李贽的眼中,都是些不要脸皮的伪君子:“讲道学者,但要我说得好听耳,不管我行得行不得也。既行不得,谓之巧言亦可,然其如‘鲜矣仁’何哉!”“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同狗彘”,就是李贽对这些人的生动概括。道学家们假装正经,摆出一副挽救世风的面孔,实际上,他们才真正是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祸首。所以李贽说:“败俗伤世者,应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
在李贽一生中,经历最尖锐的反道学斗争,是他与道学家耿定向的论战。耿定向(1524—1596),字楚侗,做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和刑部侍郎,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假道学。李贽说他:“名心太重也,回护太多也,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似这等口是心非,“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展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耿定向的朋友何心隐被统治者迫害致死,武昌数万人为之喊冤。耿定向本是有力量营救他的,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官职,避免嫌疑,不肯出面说公道话,却又把自己比作“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的东廓先生(邹守益)。所以李贽揭露他说:“东廓先生不避恶名以救同类之急,公其能此乎?我知公详矣,公其再勿说谎也。”耿定向又大讲什么“不容已”,意思是说,凡合乎正义的事情就要不避困难地去做。李贽挖苦说:“分明贪高位厚禄之足以尊显者,三品二品之足以褒宠父祖二亲也,此公之真‘不容已’处也,是正念也。”李贽选中了这个假道学为靶子进行解剖和揭露,一针见血,语语中的,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结
李贽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位进步思想家,他是封建礼教的异端和勇敢的反道学战士。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贽作为进步思想家在历史上很有建树。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清朝的唯物主义者戴震,都深受李贽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人士,也从他的著作中汲取了力量。他勇敢批判旧思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斗争精神,则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