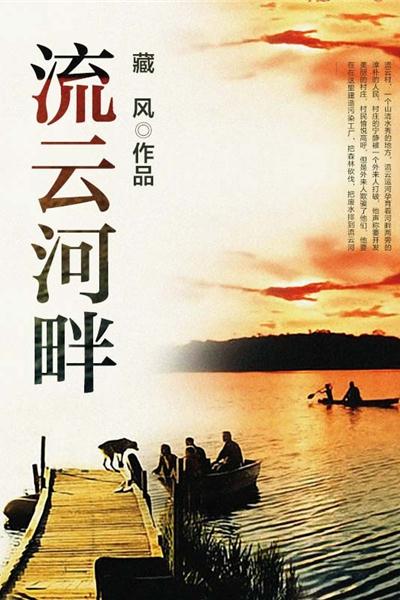1958年春节到了。这一年,我家破例没有杀猪,别的乡邻也没一家杀猪的。过去,每年一入冬,家家户户都传来猪叫声。杀头猪过年,是每个庄户人的念想。一户户人家,苦熬苦攒劳作一年,唯一的盼头就是家里养的那头猪,年关一到,将猪杀了,让全家人过个肥年。大家入了生产队,不让养猪了,集体来养,到了年关,也会杀猪,但分到每个社员头上,不过就两三斤肉……记得当时,父亲将肉提回家,脸色沉得像铁,他将那二斤左右猪肉往箱盖上重重地一摔,嘴中骂了一句,老王八犊子,将人坑苦了。
守礼看出父亲是为肉少不高兴,说道:“爹,少就少呗,谁家都那么鸡巴点儿。我弄些套儿,去套些兔子獾子,再赶些沙半鸡,咱家还能缺肉吃吗。”
守礼这些年长了不少出息,除了不爱上学,在大自然中,已经磨练成一个小猎人了。
父亲没说话,没再发脾气,算是默认了守礼的话。
守礼没吹牛,那个春节,虽然猪肉少,但守礼确实弄来了不少山兔野鸡沙半鸡鱼什么的……其中,沙半鸡和鱼最多。沙半鸡是一种小型候鸟,半斤多重,随着天气剎冷,它们成群结队地从北方飞来,在大河停留休息。沙半鸡在地面上爱跑不爱飞,守礼就是掌握了它们这个规律,见哪有沙半鸡群,在远处架起一张口袋网,口袋网旁边搭一些隐避物,然后绕到沙半鸡对面,将沙半鸡往架网的方向哄。沙半鸡见有人,便找有隐避物的地方逃,如此,很多便钻进了网里……家里仓房里沙半鸡堆了一大堆,而鱼更多,冻了一大缸,这些鱼,也都是守礼打冰窟窿弄回来的。守礼说,东大河发大水时,将鱼带上河套,水退下去后,很多鱼留在了泡子中,天一冻,打个冰窟窿,用抄罗子一搅,鱼老多了。
春节前,我和母亲商量,拿了10只沙半鸡两只野鸡和10多斤冻鱼,给林老师家送去了。林老师没在家,师母一看我送来这么多东西,眼睛湿润了,我怕她拒绝,放下东西就走了。
守礼虽然弄了这么多“肉”,但父亲依然不高兴,整个春节,我们都是在父亲沉沉的脸色中过来的。
讨厌什么来什么,开学后,嘴能吞下钢琴的李萍老师成了我们班主任。
谭斌说:“这叫麻子不是麻子,叫坑人呢。”
其实,李萍老师也没“坑”我们,这一年,我们基本没怎么上课,全参加大跃进了。
(此处略去620字)
开学不久,我们这些学生还没有适应李萍老师,校长王大胖子向我们布置了钢铁任务。王大胖子情绪激昂,唾沫星子乱飞,讲道:“现在……(此处删去80字)”
谭斌在我后面小声说:“搁鸡X炼钢?”
我制止谭斌:“听他怎么说?”
王大胖继续讲:“我经过通盘考虑,我们这里离矿山远,又没有交通运输工具,只能在身边做起,也就是说,每名学生,要充分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一周之内,每人交上10斤废钢铁,我们统一送到一线工地冶炼。”
谭斌站出来发难,道:“王校长,我家的大锅小锅都让生产队端走了,还上哪去弄钢铁?”
李萍老师也讲了自己的担忧,说道:“是呀,王校长,如果别的活儿,同学们还能出把力气,但是捡废钢铁,哪是说捡就能捡到的?”
王大胖子一锤定音:“怎么捡我不管,这是集体的决定,也是公社党委下达的钢铁任务,一定要完成。”
王大胖子说完,宣布散会,李萍老师气得脸色通红。
回到教室,李萍老师将我叫到门外,说道:“张守义,你是班长,同学们都说你有主意,你看这任务怎么完成?”
李萍老师歌唱得不好,嘴也大一些,鼻子朝天,如果不唱歌闭上嘴,低头一站,看着也算顺眼,毕竟还不到三十岁。想到学校会上,她能站出来为我们这些同学考虑,我没难为她,说道:“让我和同学们想想办法吧。”
我叫来谭斌和钟玉花,让他俩再分头找些同学商量办法。钟玉花同桌刘振清说:“有办法了,生产队敲响用的铁轨,奶奶庙烧香用的香炉,不都是铁么?我们拿回来不就行了。”
钟玉花首先赞成:“这办法好。”
“好,好什么好,这不是让同学去偷么?”刘振清姐姐刘振慧,边说边打了弟弟一拳。刘振清和他姐姐刘振慧,都在我们班。
刘振清没理会姐姐的拳头,振振有词说出一番大道理:“这怎么能算偷呢?不要忘了,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共产主义一切财富大家共同所有。社会上的东西都是大家的,我们帮着送到学校,学校帮着送到生产一线,生产一线炼出钢,再给大家用,这有什么不好?”
“刘振清说得对,是个好办法。”同学王利民说。
“完不成钢铁任务,王大胖子是不会答应的。”同学王满仓说。
刘振慧看这么多同学支持刘振清,也就没再反对。
我看着这些大胆的同学,一时不知道如何决策,犹豫间,谭斌小声对我说:“东排木有个奶奶庙,史家屯有个老爷庙,那里都有铁香炉,现在,没人烧香了,摆在那里也没什么用?还有生产队上工下工敲的铁轨犁铧,挂在那里也是个摆设。社员吃住在田里,谁还听那个?”
既然同学们都同意,我就开始分配工作了。刘振慧姐弟家在东排木,由他们带几名同学去东排木完成任务;谭斌带几名同学去史家屯完成任务;我和钟玉花带几名同学,到西崴子拉拉屯完成任务……其他同学三人一组,到附近生产队伺机而动。
最后我宣布纪律:“注意保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同学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不到一周时间,大家肩扛车拉,就把奶奶庙、老爷庙的香炉运到了学校,另外,还有几个生产队敲响用的铁轨、犁铧,甚至,还有一些同学交上了家中的破菜刀烂鞋拔子等……看着这堆东西,我沾沾自喜,领着李萍老师看同学们的丰硕成果。李萍老师听说我们完成了任务,有些不相信,当她站在废铁堆前,看着这些东西,用脚踢了踢香炉,又拿起一个鞋拔子,点点头,又摇摇头,动情地对大家说:“真是难为同学们了。”
听了李萍老师的话,我感觉,我的心又和她贴近了一层。
听说我们班率先完成了任务,牛淑芬张中原两人来找我,牛淑芬很着急,一见面就问:“张守义,你们班的任务是怎么完成的?”
我看到张中原跟屁虫一样站在她身后,心里有些酸,说道:“还不是同学们交上来的。”
“不对,你骗我。”
看牛淑芬急了,我不得不告诉了她。
牛淑芬听后,非但没感谢我,反而说,一定是你的坏主意?
“这你可冤枉我了。”
牛淑芬没容我辩白,转身就走,张中原紧紧跟在她后面。
没过两天,牛淑芬班上的钢铁任务也完成了,全校的钢铁任务也都完成了。
王大胖子校长红光满面,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做报告:“老师们,同学们啊,我们超额完成了钢铁任务。上级领导表扬了我们,这是我们学校和全体师生的光荣。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精神,去迎接上级领导交给我们的新的任务。”说完,他带头鼓起了掌,老师和同学们的掌声稀稀落落。
王大胖子没管师生反应,讲道:“现在,粮食已经收割了,为了粮食增产,达到亩产万斤,跨黄河、过长江,上级领导经过多方取经,总结出了成熟经验,要将我们的土地进行深耕。也就是说,地挖得越深,粮食的产量越高。镇领导要展开大会战,全镇人民都要深入秋翻第一线,吃住在地里,任何人都不能缺席。我们是革命学生,更要冲到第一线。”
我们这些学生,又被赶到了田野上。
当时的场面,可谓激动人心,收割后的原野,遍地都是红旗,遍地都是人流,大家挥动着铁锹挖地。高音大喇叭也架到了田间,播音员播着群众来稿,有的是自己写的,有的是抄报上的,读到哪个作者时,大家都会对他投去敬佩的目光。大跃进,不仅是粮食钢铁的大跃进,也是中国诗歌的大跃进,六亿人民成了六亿诗人,一会是“高梁红了脸,杆子冲破天,镰刀削不动,要用大斧砍。”一会是“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袋烟。”除了朗读各种歌谣,还有歌唱,我们班主任李萍老师,歌儿唱得不好,也被广播站请去,站在台上声情并茂地唱着大跃进歌曲。其实,这些歌也不用怎么唱,只要会喊就行了,如《乘风破浪大跃进》中唱道:“生产大跃进啊,大家一条心,农业纲要四十条,五年来完成,嘿,五年来完成……”
李萍老师被抽调到宣传队,班级由我管理,另外,学校还请来了一位农民李大爷,指导我们深翻地。
李大爷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民,脸色和田地差不多,也像田地一样,布满了垄沟垄台,那是岁月雕刻的皱纹。除此之外,李大爷嘴唇上干裂出很多口子,沾着血丝,看来,他在野外待很多天了。
李大爷见到我,粗鲁地说:“妈X的,净胡整,把你们也弄来了。”
我说大爷,我们没有学过深翻地,还请你多多指导。
“妈X的,深翻地,折腾人呢。我都七天七夜没回家了。你就把同学布置开,往地里挖就行了。”
我问挖多深?
“妈X的,越深越坑人。咱这疙瘩儿,妈逼的一锹好土,往里挖,除了碱土就是黄土,能长庄稼么?你就告诉同学们,把表面上的土翻松就行了。再说了,哪年不春旱,秋天将土翻开,春天怎么保墒,苗能出么?妈X的,就等着长个鸡X吧。”
有了“妈X的”李大爷指导,我将同学们组织成一排,一个人排一米宽,开始了秋翻地。
我们没有按照上面指示深挖,只是浮皮燎草地干,但是,东北的土地宽大得吓人,从地这头看到地那头,便到地平线了。刚开始,大家干得生龙活虎,挖了一阵,似乎离地头越来越远了,速度也就渐渐慢了下来。钟玉花挨着我,我挖的部分频频往她那里倾斜,但她还是落得很远,我只能将她的趟子部分都挖了。钟玉花追上我,眼神充满感激,为了证明她不是没出力,伸出小手给我看。钟玉花的小手又白又嫩,一直是我心仪的小手,现在,这双小手布满了泥巴,还有好几个黄豆大小的水泡,有两个已经磨破了,流出了血。看到此,我掏出手绢帮她把手缠住。钟玉花温驯地任由我帮她包扎,微微的鼻息吹到我的脸上,很痒。
我告诉她,跟着我,不用费力干。
钟玉花悄声说:“那哪儿行?同学们看着呢。”
钟玉花说完,脸上微微一红,马上又挥着沉重的铁锹,一锹一锹去翻土了。
看她如此,我心里不知是一股什么滋味儿。
中午时分,一辆大马车到了地头。马车上除了车老板,还有王大胖子和几位妇女,车上装着饭菜。
王大胖子招呼我们:“同学们辛苦了,学校给大家送饭来了。”
钟玉花小声叫我:“守义,你看,师母也来了。”
钟玉花不说,我也看到了师母,她围着的那条赭石色的围巾,离很远,就像一面旗帜一样地向我打着招呼。
学校安排的伙食不错,发面饼,萝卜汤。同学们排着队,依次取过饼和汤,我走近师母,轻声问:“师母,你怎么也来了?”
师母抬头看是我,微微一笑,说道:“学校的人全出去干活了,学校把我们这些家属组织起来,给你们做饭。”
师母说这话时,我看到王大胖子嘀溜溜的小眼睛,一直盯着她看。
大家挖地挖到晚上,同学们的速度更慢了,我没有催,这时,李大爷挥手招呼我,说道:“你找些人,多抱一些苞米秸子来,这大野地的,到了晚上才冷呢。妈X的,也不知抽什么风,晚上还不让回家。”
我和父亲打鱼,有过野外住宿经验,现在深秋了,在这大野地里熬困一夜,我知道什么滋味儿。我喊来谭斌,让他将所有男同学都带上,将地头摆着的苞米秸子都抱来,能抱多少是多少,最后,我加重语气对大家说:“晚上没有火,没有铺的柴,大家可要冻成冰棍了。”
黄昏时分,同学们在田间聚了很多秸杆,小山包一样,我问李大爷够不够,他说够了,我这才让同学们停下休息。
晚饭送来得很晚,车上只有王大胖子和师母。王大胖子将车赶得呼呼号号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也会赶车似的。车停下后,同学们累得没了吃饭的心思,王大胖子精力充沛,喊道:“同学们辛苦了,学校给大家送饭来了。”
晚饭还是白面烙饼,汤换成了白菜汤。
王大胖子亲自动手,给同学们发饼,师母给大家盛汤。王大胖子叫叫喳喳,师母蔫蔫巴巴。我叫了一声师母,她似乎也没听见,还把汤倒歪了,一半进了碗里,一半落到地上。我再次问她:“师母,怎么就剩你一个人来送饭了呢?”
师母这才“哦”了一声,看到撒的汤,有些不好意思。王大胖子解围:“没事儿,没事儿,咱汤有的是。”说完,又高声喊道:“同学们,汤随便喝,不够的,再来盛。”
饭吃完了,但是,王大胖子校长还不走,很热情很关心,看看这个,问问那个,最后叫过李大爷,说道:“你一定要将孩子们管好了,不能冻着。”
李大爷说:“妈X的,在家也是睡,在这也是睡,干啥不让学生回家睡呢?”
王大胖子说:“这是政治任务。”
李大爷没再争辩,安排刘振清谭斌等人,在地中间点了一堆火,又让同学们将秸杆围在火堆四周,既能坐,又能躺,还可以借火取暖。
天黑了,深遂的天空现出繁星点点,大野地里,似乎和星星比赛似的,也这一堆那一堆儿燃起了篝火……架在原野上的大喇叭还在响着,一听就是我们老师李萍在唱歌:“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愁……”谭斌说:“咱们老师平时唱歌难听,这首歌唱得最合拍儿,小寡妇哭坟似的。”我没理他,注视着师母。师母给大家盛完汤没事了,站在车边低着头,显得心事重重。身后有人拉我的衣服,回头看是钟玉花。钟玉花用头示意我看师母,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一切都安排妥当,王大胖子还不走,坐在苞米秸上和李大爷聊天。
王大胖子说:“这一回深翻,来年咱们可就大丰收了。”
“妈X的,丰收个屁,来年能不能长出苗还不知道呢。”
“人民日报说,东方红生产队,深翻地,亩产达到一万斤。”
“公鸡下蛋,母猪爬树,老虎放羊,妈X的,你信么?我种了一辈子地,啥花活儿没玩过,妈X的,搞这套儿,要真能丰收,我把脑袋种到地里。”
谭斌插话:“你把脑袋种到地里,一亩地要是长不出一万个李大爷,也保准长出一万个妈X的。”
同学们放声大笑。
“妈逼的,中国人要都像我李大爷,日子早过好了。我就不明白了,让大家平平安安过日子多好,这几年是不是谁疯了,怎么老扯咸拉淡地胡搞呢?”
王大胖子不以为忤,也就扯咸拉淡的和李大爷闲聊,听李大爷一口一个“妈X的”。
钟玉花小声对我说:“王大胖子没安好心。”
我点点头。
王大胖子又磨叽了一会儿,嘱咐李大爷看好火,注意好同学们的安全,看到不少同学累了一天,浑身打浑身躺在草堆上睡着了,这才搬起沉重的大屁股,招呼师母上车,回学校去了。
师母上车前,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似有话要说。
钟玉花一直没睡,坐在我身边,看着王大胖子将车赶进夜幕中,钟玉花悄声说:“王大胖子对师母没安好心。”
钟玉花和我同岁,女孩子在这方面有着天生的敏感。
我问道:“怎么办?”
钟玉花说:“我们去看看。”
我看同学们大部多都睡着了,李大爷也坐在那里打起了盹儿,没有惊动大家,和钟玉花钻进了夜幕中。
乡村土路坑洼不平,眼睛离开火堆,不久适应了黑暗,在星空映照下,渐渐能看清四野景物了。不知什么时候,钟玉花将她的手伸到我的手中,虽然缠着手绢儿,但我还是摸到了她的温热。我们没有说话,拉着手跌跌绊绊向前走着,心里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除了男女吸引,更有一种解开谜题的渴望。
乡村大道紧傍着防风林带,在夜色中黑黝黝的。林带里埋有很多坟冢,要没有钟玉花,我一个人还真不敢走呢。我和李大爷也学会骂人了,心里说,妈X的,你王大胖子磨蹭这么晚才走,到底想干啥呢?其实,我知道他想干啥,就像尹白驴压在串铃子身上那样,但我不确定这事儿到底能不能发生?不过,师母牟兰临走前看我那一眼,明显带有求助的意思,她一定料到了什么。
我正着着急往前走,钟玉花一下拉住我,几乎贴到我的脸上小声说:“你听——”
静寂的原野上,传来了说话声。
“别……别……”声音中带着哭腔,是师母。
另一个声音说:“还别什么?我都进去了。”是王大胖子的声音。
“你让我以后还活不活了?我要告你。”
“你告我谁相信呢?你是地主女儿,他是X派,你告我就是翻案。”
两人不说话了,传来一阵粗重的喘息声,马车咯吱咯吱动着,马套上的铁环咣啷咣啷响着。
钟玉花拉着我的手,几乎倚在我身上,问我,怎么办?
“我们为师母报仇。”想到蠢猪一样的王大胖子压在师母身上,我心里充满了万千仇恨。我撒开钟玉花的手,在附近趸磨一圈儿,看到不远处有个小坟包,坟包前立着一块墓碑。我也不害怕了,不知哪来的力气,用力一扳,就把朽烂的木头墓碑扳了下来,拿在手中,冲着声音跑去。
钟玉花紧跟着我。
声音渐渐近了,依稀中一辆马车停在林带旁边,马儿不知人间事,喀嚓喀嚓地掠着路边的枯草。马车上面,王大胖子硕大的身子压着牟兰师母,他冲撞的力头之大,使整个马车痉挛一样有节奏地咯吱着。此时,我什么都不顾了,骂了一声王八蛋,使足了力气,一墓碑,实实在在砸在王大胖子屁股上。我用力之猛,墓碑和屁股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让朽烂的木碑断成两截儿,同时,也传出了激动人心的“啪”的一声,声音之大,让人心惊肉跳。
突然的袭击,王大胖子“妈呀”一声,本能地跳下马车,本能地提起裤子,本能地逃跑……平时耀武扬威的王大胖子,一墓碑,便打出了本能的馅儿。他在前面跑,我在后面追,王大胖子胖是胖,逃跑中,把他祖宗的劲儿都使出来了,我的半截墓碑,也只撩到他的肩膀两次,虽然我很想将他圆圆的脑袋砸碎,但是,就像老师教学生写八股文一样,关键时候,开始但是了……我当时确实但是了,我想到了父亲当年打偷鸡贼的事儿,引得全家逃难……想到此,我脑袋冷静下来了。王大胖子固然可恨,还不到打死他的地步。我停下脚步,任由王大胖子气喘嘘嘘消失在夜色中。
我回到马车旁,钟玉花抱着师母,师母几乎哭得背过气去。
钟玉花一边抚着师母的背,一边劝她,无非是告王大胖子,王大胖子不得好死的话,师母一声不吭,不停地哭着。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竖在那里,听着师母的哭声,我的心愀成一团。
这种时候,女人往往更有主意,钟玉花问我会不会赶车?我说会。
钟玉花说:“那就先把师母送回去吧。”
马是匹老马,不用赶,我拉起马缰绳,它便跟着我往镇上走去。
靠屯街静悄悄的,大家能下地的,都下地了,不能下地的,也都睡了。马车进了镇东门,师母停止了哭泣,招呼我将车停下,说:“你们不用送我了,我自己回去。”
我说马上就到你家了。
钟玉花说:“师母说不让送,我们就不要送了。”
我一时不明所以。这时,师母道:“守义、玉花,我今天求你俩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千万不要说出去。”
我说师母你不用怕,我们明天就去告他,我俩给你做证。
师母说:“现在你们老师这个样子,告也白告。再一个,我也怕你们老师受不住。”
听了师母的话,我这才知道师母不要我们送她的用意所在。
看着师母迈着踉跄的步子拐入街角,我一拍马屁股,老马自己拉着车回了学校。
钟玉花声音哽咽着问:“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
我叹息一声,说道:“不知道。”
我们还得回到大野地去。
一路上,我们默默无语,经过那片王大胖子强奸师母的林带边,钟玉花停下脚步,轻声说:“守义,抱我一下好么?”我身不由主地抱住了钟玉花娇小的身子,她把脸贴到了我的脸上,她的小脸凉凉的,一片湿润,有她的泪,也有我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