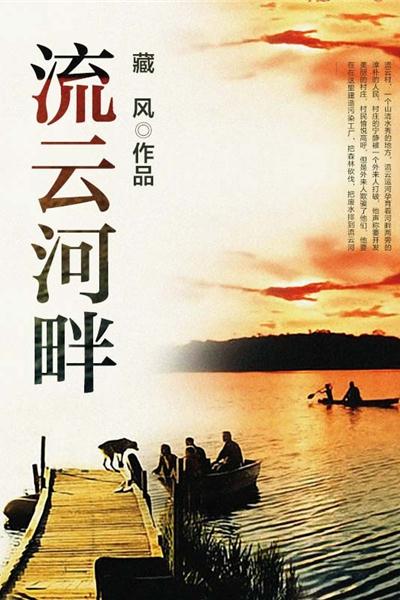林墨林老师自杀了。
林老师自杀是公安局第二天下的结论,同时,镇里和学校还组织了一次批斗会,批斗会是第三天林老师发丧前开的,会议由校长王大胖子主持。此时的林老师,由学校打的一口白茬棺材收敛了,棺材放在校园中。镇里派来两名公安,荷枪实弹守在棺材旁。王大胖子站在主席台上,面对着满脸沉重的学生老师,也是一脸沉重,他讲道,由XXX亲自领导的这场XX运动,是一场挽救中国危亡的伟大运动,是十分正确的。学校揪出林墨林这个X派,是紧跟XXXX步伐,是清理祖国健康肌体上的腐肉,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因为如此,一些X派分子不甘心灭亡,就是死,也要向祖国和人民示威,我们一定要将他们批倒批臭,扔进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讲完,王大胖子带头喊起口号——打倒林墨林,但是,下面的老师与学生,没有几个人应和他,稀稀落落的一点声音,就像声声叹息,更多的还是老师和学生的低泣声。
工宣队头头见此,和王大胖子耳语一番,宣布将林墨林老师埋葬。
学校的大马车来了,在公安注视下,几个校工和老师将林老师的棺材抬到马车上,赶向校外。
马车一动,校园里嚎哭震天。
两名公安守住校门,不住学生送行,但我和谭斌张中原,还有林老师教过的一些男女学生,不顾公安恐吓,强行挤出学校大门,跟着马车跑去。后来,一些老师也挤了出来,跟上了马车。马车穿过大街,一路向西,奔向靠屯街西面的乱葬岗子。乱葬岗子是靠屯街的公共坟地。一片坐北朝南的坡地上,长着一些乱蓬蓬的老榆树,老榆树下面,荒草凄凄,新坟压旧坟,排满了整个山坡。马车东拐西绕,来到一处新挖的坟坑前。车一停下,几名校工和提前来挖坑的人,急忙将林老师的棺材抬下,放进坑中,就开始往上填土了。
一声惨叫,师母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她披头散发,疯了一样往坟上扑着,被李萍老师和牛淑芬拉着,撒下一片天地动容的哭声……听到她的哭声,很多人都落泪了。
看到老师的坟压上最后一锹土,一个校工抱来一抱烧纸,压上坟头纸,又将烧纸焚掉。我望着灰暗的纸烟纸屑飘上天空,似乎看到了老师站在天空上,正冷峻地注视着这片悲惨的大地。我心里对老师说:老师,你走吧,我一定为你申冤。
当天下午,我将同学们召集到后山坡上。
谭斌、张中原、刘振清、刘振慧、牛淑芬、钟玉花都来了,大家还沉浸在老师死亡的悲痛中,一个个沉默无语。
我将想好的话,向大家讲了出来。
我说,我知道同学们的心情,但现在还不是悲痛的时候。老师的死,完全是王大胖子一手造成的。是他引诱林老师谈了对X的看法,却又以此为把柄抓老师X派,这还不算,他还趁人之危,多次强奸师母。林老师自杀,就是看到了王大胖子强奸师母,才将自己吊在了学校大门上。他是用自己的死,来抗议XX和王大胖子强加在他头上的暴行。
我将真相说出来,除了钟玉花没感到惊讶,其他人,全都睁大了眼睛。
牛淑芬问:“真这样吗?”
钟玉花说:“守义说得对。我们深挖地时,我和守义就发现了王大胖子正要对师母施暴,被守义打跑了。”
谭斌骂道:“王大胖子,真他妈王八蛋。”
张中原问:“守义你说怎么办?”
我说道:“我们去告他,为老师申冤。”
张中原说:“我看恐怕不行。林老师没告,师母没告,我们去告,王大胖子要是不承认,我们就是诬告。”
钟玉花说:“那你说怎么办?”
张中原摇摇头。
我说道:“现在,我们顾不得那么多了,这事儿不能压下。我们一定要为老师报仇。我们先把控告信交到镇里,镇里不管,我们就写大X报,实在不行,我们就把同学发动起来,大家X课。”
牛淑芬站出来,说道:“守义,我支持你。”
我们又商量了一阵,这才散去。
当天晚间,我谭斌家,商量着给镇X委写信,将王大胖子如何引诱林老师谈对X的看法,又抓他X派的事儿讲了,同时,也将王大胖子在林老师改造期间,趁人之危,多次强奸师母事儿说了,最后结论,林老师是忍而可忍,才将自己挂在学校大门上的……最后,将我们的想法也讲了出来,如果镇里不处理王文生校长(王大胖子),我们全体同学就X课,就上县里省里反应问题。明人不做暗事,最后署上了我和谭斌的名字。
第二天,我和谭斌来到靠屯街镇政府,将信交给了一位工作人员。回学校后,我和谭斌感觉做成了一件大事,就等着镇X委派人找我们,就等着公安将王大胖子抓走了,但是,信交上去三天了,风平浪静,好像从来就没有这回事儿。按照我的计划,我和谭斌商量,继续扩大影响,写大X报。
星期日,我将一帮朋友聚到谭斌家,给王大胖子写大X报,我们总共写了二十份。内容无非是林老师如何被冤枉,如何被打成X派,如何抗议吊死,希望大家为林老师讨回公道等等。为了给师母留下面子,牛淑芬建议,王大胖子强奸师母的事儿不写了,我同意了。
晚上,我们分头把大X报贴在学校和镇上最显眼的地方。贴完大X报,大家如同完成了一件神圣使命,十分兴奋。我们预想着,我和谭斌写的上告信,再加上这些大X报,一定会惊醒那些沉睡的人们,为死去的林老师申冤。
然而,事与愿违。大字报这枚重磅炸弹,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就像几片草叶刮到水里,连点浪花都没溅起。小镇上,高音喇叭照常播放着东方红,太阳升,学校照常上课,人们照常在忙他们该忙的事情……围观大X报的人倒是不少,但看完后,也只是摇摇头,叹息着离开了。
我计划三步中的两步,都没有引起反响,很出乎我的意料,镇上也好,学校也罢,风平浪静。
我不甘心,我不能让林老师就这样含冤而死,我一定要为他讨回清白。我再次将朋友们召集到一起,让他们分头组织学生,准备X课。但汇报结果,并不理想,两个班加起来只有三十几个同学愿意参加。而这时,张中原却突然病了,没来上学。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张中原病了的含义,他是文教助理的儿子,知道的事情比我们多。我脑袋已接近颠狂的状态,就一个念头,为林老师讨回公道。
牛淑芬说,罢X的人太少,引不起哄动,不如和他们正面交锋,如此,能引起更多学生注意,然后再X课。关健时候,女人往往比男人冷静。我同意了牛淑芬的建议。
我和牛淑芬带领同学们走进校长办公室时,工作组的头头也在办公室。王大胖子脸露惊诧,却笑着问:“同学们,有什么事么?有事让班长一人来就行了,不要这么多人来办公室。”
我心想,你真沉得住气,好像林老师的死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说道:“王校长,我们是为林墨林老师的事来的。林老师当时不讲话,是你动员他讲话,他讲完了,你还表扬他讲得好。这些,我们这些学生都能证明。但是,一转身,你就将他定为X派,直到将他逼死。”
王大胖子一听,脸红脖子粗地站了起来,似乎要打我,但我心里早让愤怒填满了,正想再揍他一顿。
王大胖子因为在校长室,又有工作组头头在,没动手,转移话题道:“大家马上回班级,有什么问题,我们会解决的。”
“别人的事情你解决,你自己的事情谁解决?”
“我什么事情?”
“你什么事情?是你诱导林老师成为右派,你又趁人之危,强奸林老师爱人。林老师无处说理,这才吊死在学校大门上。”
本来,我不想将王大胖子强奸师母的事讲出来,但一时气愤,就讲了出来。这时,王大胖子真急了,挥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这一个耳光就像是一个信号,一下将我的愤怒引爆了,我反转手也去打他,我们一下撕扯到了一起,几位男同学也都围了上来,趁机在旁踢上几脚,女同学也有发泄愤怒的方式,将王大胖子的水杯暖壶摔在地上……校长室乱成一团。
这时,工作组头头一拍桌子,声嘶力竭地喊道:“都他妈地给我住手。”
此时,我们音乐老师李萍和体育教师齐楚,也都挤进来了。李萍老师抱着我就往外拉,工作组头头骂骂咧咧:“你放开他,妈的都反了不成。”
李萍老师并没有听他的,和齐楚合力将我推向门外。
工作组头头继续在屋里吵吵:“妈的,有事儿说事儿,事儿是打架能解决的吗?你们都听好了,不管谁对谁错,我们工作组会调查的。”
听工作组头头如此说,又见李萍老师恐惧关怀的神情,我想,这事儿也只能闹到这里了,这时,牛淑芬小声对我说:“我们回去吧,让他们知道就行了。”
我和牛淑芬各自带领同学回到教室,给我们班上课的是新换的陈老师。他讲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心里还在想着校长室,想着镇里和工作组头头能否调查,想着明天如何组织学生罢课。
但就在下午放学时,张中原在操场堵住我,递给我一封信,焦急地说:“守义,什么也不用问了,赶紧逃吧。”说完,马上走了。
从我和谭斌写控告信开始,张中原就没有参加,我对他有意见,这几天一直不愿理他。张中原如此焦急,我一时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打开信,信中写道——
守义同学: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你在怪我,怪我没参加你们的活动,我没去,是我父母坚决不让我参加。我父亲说,反X斗争是XXX亲自领导的运动,没有人可以阻挡。
守义,你们惹麻烦了。你们写给镇党委的信,镇党委已经找王校长核实了,王校长不承认,牟兰也不承认,如此,你和谭斌就成了诬告。你们又写大字报,又去校长室闹,还要组织学生X课,镇党委研究,要将你俩当成首要分子打成反革命,但镇领导思想不统一,报到县里,县里将你俩定为“X倾翻案分子”。现在,镇领导全知道了,我父亲知道这个消息的,冒险让我通知你俩,快逃吧……
看完张中原的信,犹如晴天霹雳,一下把我击垮了。
这飞来横祸让我如何面对父母?如何面对同学和朋友?我一点都不敢想象,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让他们抓到,谭斌也不能让他们抓到,我带着信,急匆匆来到谭斌家。
谭斌看完信,和我一样傻了,一句话也没说,呆呆地站在那里,连他父亲从他手里把信拿走都没有反应。
谭斌父亲是位和蔼可亲的商人,在镇上有一家商店,公私合营后,交出了商店,依然在商店干。平时,他对我们这些同学非常好。他默默看着信,没说一句话,脸上乌云翻滚,似乎马上就要雷鸣闪电,霎那间,又风平浪静云收雨散了,只是说了句,这是什么世道呢?
他没责备我们,抬头看着我和谭斌道:“这么大的事儿,张中原不能撒谎。就按张中原他爸说的,你俩马上躲到外地去,不能等着来人抓走。守义,我知道你和斌儿好,但没有办法呀。老天有眼的话,以后你们还会有机会在一起的。现在我就送斌儿走,你也赶快回家逃吧,不要耽误时间了。”
离开谭斌家,我头脑冷静下来了。天没塌下来,地没陷下去,就是天塌下来地陷下去又能如何?逃,我也要见牛淑芬最后一面,我不能就这样偷偷离开。
我忐忑不安地敲响了牛同家黑色的大门,开门的是牛淑芬。她见是我,面露惊喜,拉着我就往院里走。我急忙说:“淑芬,我找你有事儿,你能不能陪我走走。”她先是一愣,紧接着跑进屋,很快换好了衣服。
夜色很暗也很静,我们在街角站下了。
一路上,我都在考虑如何对她说明原委,让她不被晴天霹雳吓倒,无论命运怎么对我,她都应该好好读书,好好生活,享受她美丽的人生。
站在街角,我平静地告诉了她发生的一切,包括我马上就要逃离的想法。黑暗中,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只感到她浑身在颤抖,最后,她不知所措地说:“守义,你不要吓我。”
“淑芬,一切都是真的,我没有吓你。”
“走,去找我爸爸,让我爸爸给想办法。”她拉着我就往回走。
我拽住她,说道:“淑芬,现在找谁也没用。镇党委因为意见不统一,已经报到县上了。县上已经定案了。来抓我的人可能都下来了?此时,你爸说话也不管用了。我现在只有逃跑这条路了。”
“你要逃哪里去?”
我说我也不知道,总之要马上逃。
牛淑芬半天没说话,似乎在考虑什么,突然,她不顾一切抱住我,抱得紧紧的,喃喃说道:“守义,抱紧我。”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们谁也没说话,任凭两颗心在一起拼命碰撞。
我不知道,我梦里有多少渴望,能够抱一下牛淑芬,但当美梦成真时,却是这样悲凉……古人创造了生离死别这个词汇,也许,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感觉吧。那拥抱,更多的是泪水,是牛淑芬的泪水,也是我的泪水……当我们脸贴在脸上,泪水和泪水融合在一起时,我们似乎都明白了,这就是我们的命,是我们朦胧爱恋结出的最后果实……从此,天各一方,暮霭沉沉,留下的也只有思念了。
我们不知道抱了多长时间,我推开牛淑芬,失魂落魄地跑开了。
我一口气跑回家中,跪在父亲面前。
我像讲故事一样,将林老师被打成X派,爱人被人强奸,林老师愤怒不过,吊死在学校大门上,以及我为林老师申冤,县里抓我X倾翻案分子的事儿……一口气讲给了父亲。
父亲坐在炕头,似乎在听一个和他毫不相干的故事,他的手,一支在捻一支纸烟,几次都没捻好,最后,总算卷成了,他把烟放到嘴里点燃,狠狠地吸了一口又扔了。这才说道:“起来吧,你做得对。做人不能忘恩。事情发生了也好,男人早晚都要出去闯荡一番的,现在大饥荒,你出去了兴许还能找到一碗饭吃。”
母亲抽泣着说:“这挨饿年头,家里都吃不饱,你让孩子上哪去?”
父亲带着火气说:“上哪去都行,就是不能上监狱。”
母亲说:“那就让守义去辽源他大姐那儿。”
我插嘴道:“行,我马上就去大姐那儿。”
父亲果断地说:“不行,你大姐那你不能去,你大哥你二姐那你都不能去。你要逃,就逃到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地方。”
“那让守义上哪儿?”
“你别问了,去拿二十块钱。”
妈妈找出钱后,父亲又支使母亲,去找点干粮。
妈妈去找干粮时,父亲打开柜子,找出一个信封,揣在兜中。
母亲将所有的干粮包了一个包,带进屋中,不放心地问:“你到底让他去哪里呀?”
父亲不耐烦地说:“别问了。”
父亲提上干粮,对我说:“走吧,我送你。”说完,率先走到了外面。
我看了看还在熟睡中的弟弟妹妹,看着母亲满眼泪水,我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流了满脸。
外面下起了雨,父亲将一件蓑衣扔给我,向院外走去。
我们顶着大雨,踩着泥泞,向东大河套走去。
走上大壕,父亲站住脚,对我说:“你十六了,是个大人了。原先,我还指望你考取大学,能有点出息……现在就别做这个梦了。”父亲说完,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和二十元钱交给我,说道:“这个信封,是老朱家你表姐家的地址,她家住在黑龙江的鹤岗,你就去那里。见了你表姐,你只要提我,她会收留你的。”
听了父亲的话,我哭了。
父亲没管我哭泣,继续道:“守义,记住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一个人在外边,一要有心计,二要肯吃苦,三不要走歪道儿。”
很少说话的父亲,一路上,给我讲了很多做人行事的道理,带我来到了回龙崴子。
回龙崴子我家的房子还在,搬罾网还在,船也在,但都不是我家的了,归了生产队。
大雨哗哗下着,看网的人早睡二道岭去了。
父亲拉过船,让我上去,说道:“你就向下漂吧,漂完了伊通河便是松花江……你在哈尔滨上岸,到哈尔滨坐火车去鹤岗”
父亲说完松开了手,小船在水流的冲击下向着下游漂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