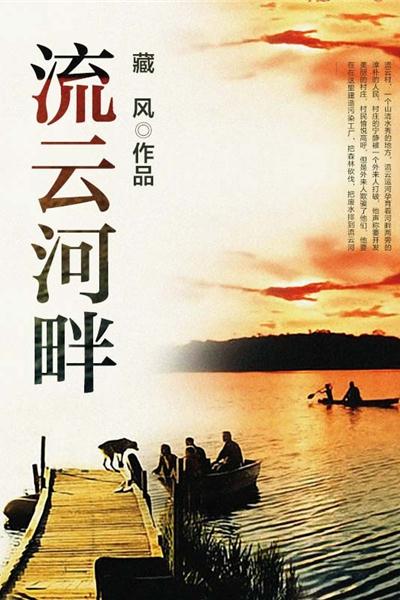时光过得很快,学校操场上的几棵老杨树,几天前还是一片翠绿,转眼间,就变成了一片金黄,在秋风撕扯中,一片片叶子叹息着飘落了下来,飘得满地都是,似乎在告诉人们:秋天到了,冬天马上就要来了。
在这个由夏天转入冬天的过程中,我们的大杂烩教师培训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郑老师和她工业局局长的丈夫离了婚,再一个,班上陆续有十几名同学都退了学。退学的原因主要是饥饿。我们的粮票由原来的三十二斤,历行节约掉四斤,变成了每月二十八斤。在缺少副食的年代,这些粮食实在填不满大家圆滚滚的肚子。那些退学的同学也是为了肚子,有的去矿上当了矿工,有的去林场当了伐木工,有的则回农村当了农民……总之,大家不论去哪里,都想找个能吃顿饱饭的地方。
而我们身处其中的东北这座煤城,好像一夜之间,便被逃荒的人群占领了。那些操着南腔北调、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人们,充塞在每一条大街小巷,那一声声撒心裂肺的乞讨声把城市的空气都喊震颤了。大批逃荒人的涌入,使小城的治安遭到了严峻挑战,各家各户的衣服被子经常被偷,而更多被偷被抢的,还是那些能够入口的东西,有些人家在城边种了些小地,一夜之间,就被人给收光了,很多副食店也都遭到了抢劫,表姐夫的粉条厂,不仅粉条被人一夜间全扛走了,就连漏粉的土豆,也一袋袋给搬光了。表姐夫气得在家大骂:妈的,土豆都偷走了,我鼻涕再多,也漏不出粉来啊。
大批逃荒人的涌入,使这个矿山小城不仅人满为患,同时也导致物价飞涨,土豆、萝卜、大白菜等蔬菜,每市斤卖到三四元钱,难得一见的粮食也被运到黑市,每市斤卖到六七元钱。过去,一直自以为财大气粗的工人老大哥,现在也成了霜打的茄子——蔫了,他们之间流行着一句话: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回家种垄葱。
我每月三十六元五角工资,也只能买十几斤蔬菜,或五六斤玉米了。同学们见面的问候语,由过去很洋气的“你好”,现在则变成了 “你饿么?”或者是“你还饿么?”
教师培训班,由教育科耿科长主抓,耿科长很负责任,隔三岔五总到培训班看看,看到我们的伙食一天不如一天,一时间也没了办法,和同学们商量怎么办?有家在农场的同学出主意说,现在正是粮食收割季节,农场收割时落下很多东西,不如我们自己去捡。耿科长一听马上决定,给我们放一周假,让我们去附近农场搞小秋收,自行解决粮食疏菜问题。
小秋收由陈嘉良倪春萍带队,工具自备,到了地点自由分散。住在本市的同学采取自愿,愿意去的就去,不愿意去的就不去。如此,除掉不去的我们还有三十人。郑老师没有和我们同去,临行前,一再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我们一行三十人,扛着从本市同学家借来的镐头、二齿子、三齿子,拎着土篮子,腰里揣着布袋,推着地排车就出发了。我们的队伍很壮观,按照学校体操的队形排着队,像学生又有很多年岁大的成年人,像盲流又穿得很齐整,像捡秋的队伍又这么整齐庞大,一路上,很多人向我们投来了疑惑的目光,弄不明白这是一支什么队伍?
按照农场同学指点,我们去了新生农场。新生农场是一座很大的农场,半军事化管理,农场职工都是一些劳教人员,很多都是从京城发配到这里的犯人,(删去六十字)另外,一些刑满释放人员无处安排,又在此就业了。这些人每天被人押着,在此开荒种田,多年后,从公开的报刊中知道,很多文化名人当年都在这里关押过,如丁玲、艾青、聂绀弩、丁聪、吴祖光等……但当时不论是我,还是同学们,脑袋里想的只有粮食,或粮食的替代品——土豆,并没有人去关心或者去想这里都关了哪些名人(删去八十字)?
真让农场同学说对了,收割后的田地里,到处都是遗漏的粮食和疏菜,人们如此疏忽,并非这些地是犯人种的,有意遗漏,主要是东北的土地太博大了,又是机械化收割,抬高走低的,很多粮食都被落到了田地里。
我们来到一片土豆地,这片土豆地很大,有十几平方公里,除了地中间长着几棵孤伶伶的树外,或者有些地方露出几块搬不走的大石头,余下的都是被翻开的黑土。土豆地里,已有一些先我们而来的遛土豆的人,三一伙俩一串的,各自为政,自己随便找一块地往下刨着,从土里寻觅救命的土豆。进了土豆地后,我们这些同学便自由散开了,谢玲和我寸步不离,山东秀才鲁余粮和陈山月走到了一起。大家开始遛起了土豆。当地人,管我们这种捡土豆的方法叫遛土豆。这个“遛”字大有学问,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地里死死地挨着往土里刨,要多走走,有些地方土层暄软,被犁过了,被人刨过了,落下土豆的可能性就极少,有些地方硬硬的,或是犁铧翻土时走飘了,只在土层上刮了一层浮土,土豆照样还埋在土里。干了一会儿,我们就都找到了窍门儿,哪块儿土硬便往哪儿刨。这样的经验很管用,有时找对了地方,一二齿子刨下去,就带出来一堆白花花的土豆,有时刨到一个大大的土豆,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欢呼声,谢玲和陈山月还要对比一下,看谁刨的土豆大。
夕阳西下时,我们在地中间已堆了很大一堆土豆,就在这时,我们前方出现了一幅不和谐的画面:一位身材瘦弱的女人,脸色灰黄,好像正在生病,她背上背着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孩子被紧紧用背带绑在背上,孩子断断续续地哭着,但是女人并不理会孩子的哭叫,艰难地举着二齿子,一下一下刨着,刨两下,就蹲下喘会儿气。女人身后,还跟着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女孩三四岁模样,吃力地拖着一个大筐,筐里有十几个土豆,小女孩边拖着筐边往嘴里塞着生土豆。看到这幅画面,我的心一阵颤抖。这时,谢玲和陈山月一声不响,从我们筐里捡出二、三十斤大土豆,一下子全倒进了女人筐里,在女人惊讶的目光中,她俩逃离一样跑了回来。
太阳下山后,老夫子招呼大家收工,我们把土豆捡到袋子里,装了满满一地排车,推着往回走去。
路上,山东秀才鲁余粮叹息着说:“这XX怎么了,地里这么多吃的,大家怎么还挨饿呢?”
老夫子提出了一个让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可在当时,谁也回答不上来,甚至是能回答上来也没有勇气说出来。(删除一百二十字)……就像我们遛的这片土豆地,如果是个人的,早捡得一个不剩了,哪还会落下这么多土豆。
我们连续检了六天秋,取得了丰硕成果,学校的大仓库,让我们捡的东西堆满了,土豆、白菜、萝卜、大头菜、芥菜,还有少许的玉米和黄豆……虽然粮食少了点儿,但这些蔬菜,足够我们吃一冬了。
郑老师没有参与我们的小秋收,但每天晚上都来看我们,看到大家安全回来了,才放心回家。
最后一天晚上,郑老师又来了,她摸着陈山月和谢玲磨出血泡的手,说道:“同学们,你们小秋收很有成绩。我看这一冬没啥问题了。同学们都累了,明天就不要去了,好好休息一天,后天开课。还有一件事,本市不在班上吃伙食的同学,此次参与了小秋收活动,一会儿和陈嘉良商量,该你们分多少,你们拿回去。”
郑老师刚讲完,陈山月马上说:“郑老师,同学们,我家在本市,也参与了小秋收。但我声明,我不会往家拿一个土豆一个萝卜的。家里再难,也好对付,我就算支持住宿的同学了。”陈山月说完脸红红的,很激动。
倪春萍好像落在陈山月后面有点不痛快,大声说:“我和陈山月一样,什么也不往家拿。”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家住本市的同学,都喊出了“我也一样”的话语。
郑老师带头鼓掌,同学们也跟着鼓起掌来。缓解挨饿的小秋收,把同学们的情谊拉得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