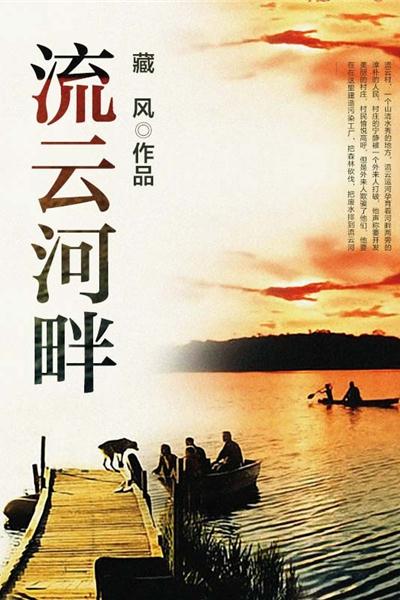母亲骂父亲胡子根儿,是有缘由的。
大清末年,资源丰富的满洲(东北)成了列强眼中的肥肉,为了争夺满洲,列强之间也在狗咬狗。日本多年来处心积虑要将满洲、高丽、蒙古变成日本的远东大陆,哪料俄罗斯捷足先登,一条中东铁路成为插入满洲心脏的一柄宝剑,他要将满洲变成他的黄俄罗斯。1904年,大清划出大辽河以东,让俄罗斯、日本在此交战,大清保持中立……大清如此,心下里不过是希望让战争消耗双方实力,以此拖延交出这块祖宗宝地。
一场日俄战争,也让多年来浸淫在皇威中的满洲百姓睁开了眼睛,他们见皇帝不管他们了,一个个拿起武器,以求自保。
住在辽阳城的我爷爷张廷祥,也趟了这淌浑水儿。
辽阳城,是日俄战争中的重要争夺目标。日本和俄罗斯,为了打赢这场战争,都派出大批间谍,拉拢大清百姓帮他们打仗。中国人实惠,谁给钱就说帮谁,拿了钱一转身儿,人没了。我爷爷也是如此,他刚从日本人那里收了钱,又去给老毛子(俄罗斯人)赶马车,帮着运送枪支、弹药,看到老毛子出现败像,他大鞭杆儿一挥,喊了几声“喔——”,大车一转弯儿拉着枪支、弹药溜家去了。战后,东北胡子(土匪)起来了,我爷爷在家中是老大,他下面还有五个弟弟,正好够一伙绺子(胡子帮儿)。我爷爷六兄弟,忙时种地,闲时抢劫。后来,东北大大小小的绺子都被张作霖收编了。我爷爷带着他的几个弟弟也入了行伍。我爷爷在奉军中干了一段时间,娶了他连长的妹妹,退出行伍回家过日子去了。我爷爷靠着大舅子的关系,在辽阳城开了一家烟馆,又在乡下买了几十亩田地,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儿。
我奶奶姓关,满族人,和我爷爷结婚后,为我爷爷生了三个儿子。我爷爷给他三个儿子,依次起名叫万田、万林、万山,从这些名字看,多少都带有一些江湖的霸气。
我爷爷过了十几年太平日子,一年秋天,他背着钱搭子去乡下高丽冲收租,晚上喝完酒回来,半路上被人背了死狗。
“背死狗”是一种抢劫方式。
强盗趴在暗处,见有单个行人,凑上前将个绳套往人脖子上一套,背起就走,将人勒死后撂地劫财。
爷爷死后,老大张万田老二张万林,天天腰里掖着枪,说要寻找仇家,仇家没找到,自己却干起了仇家的够当——当起了胡子。一次抢劫犯案,被官府缉拿,张万田和张万林,带上他们10岁的弟弟张万山,也就是我的父亲,从辽阳一路逃到了吉林。
多年前,他们三兄弟的二姨,嫁到了吉林隆安(农安)的四平街,他们便是来投奔这个二姨的。哥仨儿来到四平街,看他们二姨家的日子过得一般,而我父亲年岁又小,大哥俩一商量,将我父亲扔给二姨,两人说出去找活儿,一杆子蹿没影了。
穷人家哪有养闲人的。父亲的二姨看他也能干活了,便去地主家揽下一群猪,让他放牧。东北养猪古有传统,满人先祖通古斯便是牧猪人的意思。父亲给地主放了一年猪,第二年,两个哥哥捎来一包钱,还捎来话,让我父亲上学。如此,父亲读了三年半私塾,后来,两个哥哥再没捎钱来,他不得不终止了学业。
父亲不甘心就此退学,追问他二姨,才知道,他两个哥哥离开他后便当了胡子,两人还拉起很大一伙绺子,在北满(黑龙江)一带活动。父亲离家出走,到北满找了半年多,打听到两个哥哥那伙绺子被官兵打散了,这才无奈地回到四平街。
父亲回到四平街,给地主当了长工。
父亲很能干,头一年还是半位子(和大人一样干活,只给一半工钱),第二年就成了打头的(带工组长)。父亲给地主家扛了几年活,攒下些钱,自己拴了一辆马车,做起了小买卖。当时东北农村,家家户户使用的器皿,都是黑泥烧的黑陶,这些东西既笨重又易碎,常常需要更新。我父亲看是个来钱道儿,开始走乡串户贩卖泥瓦盆,同时,还去河边上些小鱼,也顺便卖了。
父亲精于算计,从不乱花钱,把挣的每一分钱,全买了田地。
父亲到了二十五岁头上,在四平街已有了四十多亩地,农忙时,还要雇几个伙计。那时农民爱置地,除了地是根本能让人吃饱饭,再一个那时东北遍地胡子,见啥抢啥,田地却抢不走。父亲“张海怪”的绰号,就是这时被人传开的。
父亲二十五岁这一年,结婚了。
父亲娶的是牛家坨子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
说外公家是大户人家,并非他家多有钱,主要是人口多。打我记事起,牛家坨子半屯子人,都是外公家族的。外公家是满族,姓佟,属正黄旗,但满族那些血性,传到外公这一辈上,早就传没了,因此只能当个租地户。租地户,就是租下地主家的田地,全家人干也请长工干,就像现在的大包公头儿。外公一家人缺少血性,外婆却是例外。外婆是汉人,能说会道,是屯里的场面人儿。一次,外婆去靠屯街赶集,遇上父亲赶着马车经过,外婆求父亲捎她一程。外婆坐到车上,和父亲天南地北一唠,父亲啥底细都被她摸去了。第二天,外婆打发媒人登门,订下了母亲和父亲的婚事儿。
外婆生有四个儿子三个姑娘,母亲在姑娘里排行老二,屯里晚辈称呼母亲,都习惯叫二姑或二姨。母亲更多地继承了她父亲的性格,老实、善良,又特别勤劳。父亲能娶得母亲,不但娶回一个年轻(母亲比父亲小八岁)漂亮的妻子,也娶回一个好劳动力。
母亲一生中,生有五男四女九个孩子,要将这九个孩子养活养大,母亲这一生的操劳可想而知。
父亲结婚后,在母亲扶持下,家业更加辉煌,但是,到了1946年,他突然张罗着卖房子卖地,要回辽阳老家。
父亲的决定,让人目瞪口呆,其中缘由,只有母亲知道。
原来,父亲在四平街得罪了人。
父亲家大业大,除了遭到同村人的觊觎,也是小偷小摸惦记的对像。
一天半夜,传来鸡叫声,来贼了。
父亲拎起一把打草的大钐刀就去抓贼。贼抓了一口袋小鸡,逃进了青纱帐。父亲提着大钐刀追进青纱帐。父亲用钐刀将贼打得遍体鳞伤,贼这才扔下鸡,趔趔趄趄地逃了。
第二天,屯里传来冯老疙瘩得暴病的消息,说是传染病,不让人看,不到三天就死了。自此,冯氏家族的人遇到我父亲,眼神冷冷的。父亲不糊涂,知道他打的贼是谁。
当时,伪满洲国刚刚倒台,东北成了乱把地儿。冯氏家族在四平街是个大家族,父亲担心冯氏家族报复,这才草草地卖了房子和地,将三套马车换成三套骡子车,在骡子脖子上系上红绸子,拴上串铃,带着不无显摆的心情,拉上老婆孩子回辽阳老家光宗耀祖去了。
我父亲张万山,能算计来骡马田地,却算计不了时势。1946年,正是东北打成一锅粥的时候,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红军,日本残兵,二鬼子(朝鲜流民)、白匪(白俄)、胡子……每一天,都在这片土地上撕杀着。父亲带着全家,赶着他的大骡子车,刚到公主岭,就遇到了一伙穿着灰衣服的八路军,将他三匹骡子征用了。一位老兵看到这一家人可怜,费尽心机给找来一头老牛。父亲将老牛套上车,又带着家人上路了。
父亲赶着牛车一路摇晃,到了郭家店时,遇到了穿着破衣烂衫的胡子。和胡子从来没有道理可讲。胡子不但将牛卸下杀肉吃了,还将他们带的大包小裹,全都抢走了,而且,对每个人强行搜身,除了大姐又哭又闹,母亲临行前缝在她肚兜里的钱没被搜走,父亲所有的家业,被抢个净光儿。
一家人,靠着大姐肚兜里那点钱,费尽周折,挪到了辽阳城。
辽阳城已经没有父亲的家了,他们哥几个逃跑后,烟馆被没收,奶奶嫁了人,和她的后老伴儿,搬到了乡下高丽冲去住了。
父亲带着全家找到高丽冲,和他继父理顺了父子关系,在高丽冲落下脚来。
父亲带着一大家子,在高丽冲靠采山度日。
一家人在高丽冲紧衣缩食生活了一年多,父亲感到狭小的高丽冲,远不如吉林生活好过,又带着全家返回到了吉林。
父亲带着全家回到吉林时,四平街已无处落脚,父亲只好投奔到牛家坨子的外婆家。
看到走时那么风光的一家人,一年多回来,落得和逃荒的差不了多少,外婆的家人,没有不吃惊的。
母亲讲了这一年多的遭遇,亲属们听后叹息连连,抹着同情的眼泪……同情归同情,眼泪归眼泪,谁愿意接待一无所有的一大家子呢?先是大舅妈二舅妈吵个不休,继而三舅妈四舅妈大打出手,接踵而至的,是四个舅舅对父亲母亲一通埋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愿意接纳这已沦为乞丐的一家子。
外婆家四个结婚的儿子都在一起过,如此一个大家庭,没有一个实力派掌权人,是很难将一家人拢到一起的。这个实力派掌门人就是外婆。外婆拿着大烟袋,站在当院,指桑骂槐一通骂,无论是四个舅舅还是四个舅妈,全都碾子砸到磨盘上——牢实(老实)了。
外婆让人将家中装杂物的偏厦子打扫出来,这便成了我们落户牛家坨子的第一个家。
父亲带着全家回到牛家坨子三个月后,土改的风暴吹到了牛家坨子。
牛家坨子虽然是一个屯子,但屯中的田地,大部分归县里一个叫三盛玉的大地主所有。三盛玉是满清贵族,大清初期,附近的荒野全是他家的马场,大清晚期,他家招募农民屯荒交租。到了三盛玉这一代,他家已是农安县最大的地主了。三盛玉信佛,吃斋行善,家里建有很大的一处“花子房”(东北管乞丐叫“花子”)。每年冬天,他家的“花子房”常收留上百名花子。土改时斗地主,三盛玉和他儿子,被土改工作队给枪毙了,爷儿俩的万亩良田、十几房老婆、数不清的家产,全分给了农民……我父亲讲起三盛玉的命运,不胜唏嘘,但种起三盛玉的田地,一点也不含糊。
有人说,不得不佩服张海怪,他要不回辽阳老家折腾一趟,不打成个地主,也保准是个富农,现在,居然还弄了个贫农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