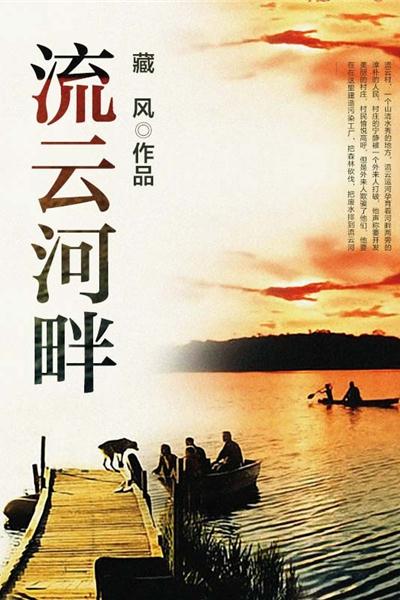快乐的暑假很快过去了,新学期开始前,我父亲做出一项决定,不让大姐二姐读书了。
父亲做出这个决定,是夜里和母亲讲的。
这天,大哥大姐带着弟弟妹妹们,回牛家坨子去了。我没走,和父母睡在大河套里。半夜时,父亲出去起趟鱼,回来时,坐在炕头吸着旱烟,他吸了几口烟,对母亲说:“就要开学了,我想过了,香兰和美兰,就不要去上学了。”我家的姑娘都带一个“兰”字,香兰和美兰,是大姐二姐的名字。母亲一听,坐了起来,问道:“孩子读书血奔心的,干啥不让念了?”父亲说:“干啥不让念了?河套这一摊放不下,家里又一大摊子,都需要人手。老国和我商量了,过年就将香兰娶过去。老国说,香兰爱读书,嫁到他家,还供她读书。”
母亲叹息一声,躺了下去,小声问:“守仁、守义呢?”
“守仁念书半桶水,在学校混岁数吧。守义脑袋聪明,我们重点供他。”
母亲再次叹息一声,道:“你呀,就是偏心眼子。”
父亲说:“念书,也要看个人情况。有能力就念,没能力念也白搭。”
父亲母亲说完这番话,都睡下了。
我躺在热热的炕上,却睡不着。我为大姐二姐感到不平。大姐是我们家老大,也是我家长得最漂亮的姑娘。大姐的性格像外婆,能说会道,对人热情,有时家里来人了,父母不在,她也招待得头头是道儿。父亲讲的老国,姓国,大家便以老国称呼他。老国是个小业主,在靠屯街烧窑做香。我父亲过去贩卖的泥瓦盆,都是老国家的产品。长期合作,老国和我父亲关系处得很好。大姐下生不久,就被父亲抱着和他家订了娃娃亲。老国的儿子很老实,也很懒。大姐懂事后,对这门婚事不满意,要退婚,父亲说:“香兰,你听好了,有我在,你就不要想别的。”父亲的话,在我们家从来都是圣旨。对此,屯里也有过流言,说我父亲和老国的媳妇好过,这才将姑娘许配给人家。传言归传言,谁也没见过真的,就连母亲,也没过问过。相对大姐来说,二姐的性格比较懦弱。二姐小时候出过天花,虽没留下麻子,眼睛却不好,看人时总爱眯缝着眼儿。也许正是这一缺陷,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外头,总受人欺负。
大姐在家不念书了,嫁到婆家还能念书,二姐不念书了,这辈子就没希望了。事实上也是如此。2013年,二姐临去世前,对这辈子没读上书,还是耿耿于怀,她拉着我的手说:“我这辈子没啥出息,都是咱爹坑的。”
我在为大姐、二姐抱屈中睡着了。
开学后,大姐二姐不上学了,就连大哥,应个名在上学,却是家里有活在家干,家里没活了,才背着书包儿撅搭撅搭去学校。
受大姐二姐退学的刺激,我学习很努力,二年级时,还当上了班级的学习委员,后来,又当选为少先队长。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很高兴,对我一番夸奖,就连父亲的脸上,也有了笑模样。我知道,这就是父亲对我最大的奖励了。
看到父亲有了笑模样,我决心再往前一步,不仅要考全班第一,还要当上班长。
我想当班长,要跨越的障碍就是牛淑芬。
牛淑芬是是我们班的班长,家住靠屯街。人姓牛,人也牛。在我们这些屯里孩子眼中,就是一个公主,家庭好,长得好,穿得好,学习好……也许,因了这些好,对我们这些屯里孩子,总是爱搭不稀理的。
我要当班长,就要有支持者。
我们班,和我最要好的同学中,男同学有谭斌和张中原,女同学有钟玉花。张中原的父亲是镇文教干部,谭斌的父亲是镇供销社主任,钟玉花的父亲是镇兽医。他们的家境,都比我家好,又都住在镇上,不知为何,对我却都很好。一天,我借一个不满牛淑芬的理由,委婉地提出要当班长,张中原、谭斌没表态,钟玉花马上说:“张守义,你肯定能当班长。牛淑芬除了能得瑟,啥比你行。”
钟玉花如此说,张中原、谭斌也都表态,支持我当班长。
我要当班长,虽然有我的几个铁杆朋友支持,还必须有更多的支持者。我们班,同屯同学不少,大多又都是我的亲属,但都窝窝囊囊的,一个个都是说话不顶硬的主儿,唯一一个不是我亲属说话也顶硬的主儿,性格又太倔,不知我能不能说服她?这个人,我是我打死她家鸡的串铃子。串铃子大我三岁,也是和我一起上学的同学。自从我和守礼打死她家鸡,她家我是不敢去了,但和她还说话儿。
串铃子是个标准的美人儿,鼻直口方,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两排白牙,盈盈闪光,只要她一张嘴,好像就能听到她银铃一样的笑声。串铃子长得漂亮,却野性十足,不论在屯里还是在学校,没人敢惹她。刚上学时,几个调皮小男生不知深浅撩骚儿,被她拿着棒子追得满操场逃。
如果串铃子能站出来支持我,班级里,谁敢不服?
一天上学,我看串铃子在前面走着,马上追上去。在学校,我叫她王长玲,在校外,我还叫她串铃姐。我放烟幕弹:“串铃姐,和你说个事儿,咱们班有同学要选我当班长,你说我当呢还是不当?”
串铃子一句话,差点把我撞进壕沟里。
“操,那XX玩艺儿,当不当能咋的?二榔头,你就好好学你的习得了。”
二榔头是我的绰号,想不到我上学了,她还这么叫。串铃子这句话,气得我想骂她祖宗,现实是,只能蔫蔫地退到她屁股后,从心里诅咒她:等你落到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想不到,没用我收拾,就有人收拾她了。
收拾她的是她老爹王麻子,还不是一般的收拾。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带着守礼在高粱地里打乌米。乌米是高粱穗受真菌感染,长出的一种真菌。乌米嫩的时候长得白生生脆生生的,可以生吃,味道甜丝丝的。我和守礼将一片高粱地溜完,两手空空,乌米都让人打走了。我们刚走出地外,就见李强气喘嘘嘘地从小毛道上跑了过来。
李强是屯里李大寡妇的独生儿子,也是我的同学。他看到我们哥俩,急三火四地说:“诶,告诉你们一件事儿,尹白驴和串铃子高丽沟子里XX呢。”
农村孩子说话粗俗。
听说有这等事儿,我马上兴奋起来,说一声“走”,便在李强带领下,朝高丽沟子跑去了。
高丽沟子是日本人占领东北时,引来朝鲜开拓团在此种水稻开的引水渠。日本人败退后,朝鲜人也走了,那些引水渠却留在那里,成了一些干沟子。
尹白驴也是我家邻居,中间只隔着王麻子家。尹白驴大号叫尹铁山,长得黑,又不爱洗脸,却被屯人叫成了白驴。说起来还有个典故。最先大家叫他尹黑驴,还编排了一个“四大黑”:新挖的煤,上锈的镐,铁山的脖子,黑驴吊。尹铁山不爱听,谁念叨和谁急。屯人知错就改,将黑驴改成白驴,这回他不和人干了。尹白驴黑是黑,却也有能耐,是屯里的猪大仙(萨满)。前面讲过,东北是满金故地,萨满之乡,人们相信万物有灵,狐(狐狸)黄(黄鼠狼)灰(蛇)柳(柳树)都有人信,除此之外,不有一些偏门左道,如尹白驴信的便是猪,别人家的神牌上供着狐狸或黄鼠狼,他家神牌供的却是猪……同时,还请猪仙给人治病。庄户人家,泥土里刨食儿,一身泥满身灰,又不爱洗澡,因此,很多人都长疙瘩疥子,如此,就求到尹白驴了,他哼哼呀呀唱一段神曲,将治疗者唱迷糊了,然后上去一口,咬开疙瘩疥子,用嘴吸出脓血,再端起准备好的泔水桶一顿喝,又一顿呕,呕出几包小药,给治疗者服下……说也怪,那些治疗者治一个好一个。也因此,尹白驴也能常常收点礼,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尹白驴比我父亲小几岁,按屯邻亲论,我和串铃子都叫他叔……想到这样一个人和串铃子XX,我心里气就不打一处来。
李强带我们来到了高丽沟子。
李强没说谎,两人果然在沟底呢。
尹白驴将他的一件黑夹袄铺在沟底,压着串铃子,正猪一样往前拱呢……尹白驴越拱劲头越足,身下的串铃子被拱得直哼哼。
我们偷窥了半天,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喊了一声“打”,李强、守礼听令,搬起土坷垃就向尹白驴砸去。尹白驴拱得忘乎所以,被突然降临的土坷垃砸得懵头懵脑,也没看清我们是谁,拉起裤子就跑。尹白驴一跑,李强、守礼小狗一样更逞强了,拿着土坷垃就追,一会儿,全钻进沟边高粱地里去了。
突然的变故,串铃子吓呆了,起来坐在那里,裤子也忘了穿。
当她抬头,看到站在沟子上的是我时,脸上现出恼怒的神情,说道:“是你,二榔头?”
串铃子没有羞赧的表示,相反,我的脸却热热的。
我撇开自己,说道:“李强说尹白驴欺负你,我就来帮你了。”
串铃子“哼”一声道:“用你帮?”
说完,她可能感到不对劲儿,缓和了下语气,说道:“守义,你不会说出去吧?”这回不叫我二榔头了。
我天真地说:“他欺负你,你回去告诉你爹。”
串铃子说:“不能告诉我爹。尹叔对我好,我愿意和他玩儿。”
我说道:“让大人知道了,还不打死你。”
串铃子说:“我愿意,谁管得着。”
串铃子说完,似乎意犹未尽,也许是怀柔政策,柔声对我道:“守义,你下来。我知道你对姐好,姐也让你玩一回儿。”
听完串铃子这句话,我感到脸上“腾”的一下更热了,嗓子干干的,裤裆也不争气地挺了起来。但是,也许当时我的性意识还未觉醒,再加上面对的是我害怕的串铃子,又怎敢造次?我一本正经地说:“串铃姐,我不会对别人说的。我也告诉李强和守礼,让他们也不说。”
说完,我义无返顾地离开了串铃子,好像我是一个大英雄。
我说到做到,没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儿。在我嘱咐下,守礼和李强也没和外人说,可不久,事情还是暴露了。
想来,串铃子和尹白驴已不是一次两次了,至于王麻子是怎么发现的?没人知道。王麻子将尹白驴叫到他家,当着尹白驴的面儿,将串铃子捆起来,用他的神鞭一下一下抽着串铃子,也不知道抽了多少鞭子,尹白驴实在看不下眼了,答应将他家的大黄牤子(公牛)给了王麻子,王麻子这才停下神鞭。
串铃子用自己的身体挣了一头牛,却再也没脸上学了。
从此,尹白驴在屯里又有了典故:小牛惹祸,大牛顶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