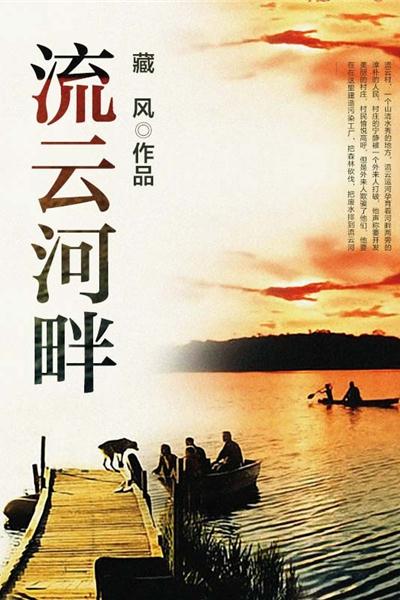我一心当班长,班长没当上,学习倒上去了。从三年级到五年级,每次期末考试,我都拿全班第一名,如此,班长牛淑芬对我也另眼相看了,班级有什么事儿,还主动和我商量。她这一热情,我再想取代她当班长,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牛淑芬对我转变了看法,我以前看她不顺眼的地方,一下子也变了:家庭好,人家有福;长得漂亮,看着顺眼;衣服好,有钱干啥不穿;学习好,人家努力了……直到写这部书时,每每想到少女时代的牛淑芬,我都会联想到秋阳下盛开的大丽花,热情似火,有一股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
随着接触增多,我和牛淑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而让我更靠近她的,是一次她竟然将我领到了她家里。
牛淑芬的家,对我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高房大院,青砖灰瓦,屋里还有电灯……等牛家坨子有了电灯时,已是十几年之后了。这样的人家,住的自然不是一般人物,后来我才知道,牛淑芬的父亲叫牛同,是靠屯街的副镇长,她母亲是防疫站站长。
牛淑芬将我带到她家去,说要借书给我看,当时,我正在拼命地看课外书。
牛淑芬的母亲,一位长得干净、漂亮的女人,听牛淑芬介绍我,笑着说:“你就是张守义啊,我家淑芬常说你,说你学习好又聪明,以后,可得多帮帮我家淑芬啊。”
牛淑芬母亲的话,让我心里很得意,但我毕竟是个乡下小子,一时间,脸憋得通红,不知道说什么好。牛淑芬见了,不管不顾地将我拉向里屋——她父亲的书房。
牛淑芬家的书房也是会客室,除了桌椅外,更多的还是书。靠墙一个大书柜,里面的书摆得满满的。一户人家有这么多书,我还是头一次见过。我家也有书,大多都是我父亲看的唱本,也只有一纸笸箩,被母亲宝贝一样锁在柜子里。看到牛淑芬家的书,我眼睛不够用了,从书柜这面看到那面,又从那边看到这边,这些书,除了马恩列斯毛著作外,大多都是文学作品。
牛淑芬看我不眨眼地盯着书,说道:“守义,这些书,你愿意看啥就拿啥,别弄丢了,这是我爸的宝贝。”
我连连点头。
我当时文学知识有限,看到一套四卷本的《静静的顿河》,翻开看了几眼,马上把我吸引了,把它当成了首借书。1965年,《静静的顿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那之前,我就看过这部书了。《静静的顿河》描写的乡村风光,很像我家的大河套,人也像,顿河边生活的是一群哥萨克,这些人的祖先都是多年前从城市逃出来的贫民,哥萨克的意思就是追求自由的人,而东北这片土地上的人,除了满人,也都是流放者和闯关东的人,也是一群寻求自由的人。
我和班长牛淑芬成了好朋友,我另外的几个朋友不理解,尤其钟玉花,说话能让人酸掉牙,道:“张守义呀,你可小心了,牛淑芬的爹是牛魔王,她是铁扇公主,你别让这爷俩给吃了。”
“牛淑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不信,你们和她处处就知道了。”
在我拉拢下,我几个朋友和牛淑芬不知不觉也成了朋友,钟玉花也不酸了,课堂上,一声声班长叫着,课堂外,一句句淑芬姐叫着,声音甜腻得能让人摔个跟头。
同学对我好,我也想报答一下同学们,但我家和镇上的这些同学家相比,可谓天上地下,唯一让我骄傲的,就我家的大河套。我想将同学们请到大河套玩儿,但是,必须有父亲的批准,没他的批准,啥样尴尬的事儿,他都能做出来。
有了这种想法,我一直在寻找机会。
一天,站在河畔上,看到父亲又在起扳罾网了,网一露水,就看到一条七八斤重的金黄大鲤鱼,在网底跳着,溅起无数水花……我帮着父亲,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大鲤鱼弄进鱼囤子里。
一条大鲤鱼,让父亲心满意足,他擦一把脸上的汗水和溅上的河水,对我说:“儿子,咱家有这样的日子,给个皇帝都不换。”
我赶紧溜须拍马:“那是呢。我镇里的同学,听我讲咱家的大河套,一个个馋得不行,都想来看呢。”
父亲心情愉快,答应得也痛快,说道:“想来就来呗。你看咱家,满地都是粮和菜,满河都是鱼,还在乎吃吗。”父亲说完,话锋一转嘱咐道:“来可是来,你不能让他们下河洗澡,淹死了,你爹可赔不起。”
“这么深的水,借他们个胆儿也不敢啊。再说了,他们都是旱鸭子,哪个也不会水。”
周一上学时,我就通知了我的几个好朋友,告诉他们周六到我家大河套玩儿。大家一听,都答应一定来。于是,他们就像我一样,心里有了念想,天天都盼着周六。周六下午一放学,我便带着他们奔向了牛家坨子。
大门口,守礼正对着大杨树练弹弓呢。这小子弹弓越来越精进了,刚飞到树尖一只指肚大小的柳莺,都被他打下来了。看到我带来两男两女——谭斌、张中原,牛淑芬、钟玉花四个同学,守礼吹一声口哨,痞气地一歪头道:“哟,还真来了。大姐二姐没白忙活,饭菜都做好了,将我捡的野鸭蛋也煮了。”
我拍一下守礼的头,将大家领进家中。
几个女生,牛淑芬钟玉花加上大姐二姐,一见面,就哇哇啦啦唠开了,尤其二姐,和大家又是同学,见面就更亲了。大家讲了半天,钟玉花才想到二姐退学了,拉着二姐的手刨根问底:“美兰,你书念得挺好的,咋就退学了呢?”
二姐神情黯淡下来,不无伤感地说:“因为啥?因为我是姑娘呗。”
二姐的话充满无奈,一时间,把大家弄得很尴尬。
大姐见气氛不对,接过二姐的话:“我父亲也是没办法。我们家兄弟姊妹多,又住在农村。爸妈一天到晚干活,既要种地又要看网,孩子们哪能都照顾到。”大姐说完,抱起还在炕上爬的四妹,继续说:“我三妹雅兰让我妈领河套去了,这个小四妹玉兰才六个月,一会儿也离不开人。”
大姐如此说,钟玉花没再问什么。
晚饭大姐二姐尽心准备,有鱼有野鸭蛋有蘸酱菜,但大家吃得都很沉闷。大姐、二姐辍学的遭遇,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一道阴影儿。
晚饭后,我说去看外婆,顺便告诉表哥佟万贵、表姐佟玉华明天一起去河套,我的几位同学一听,都跟着去了。
外婆看到我们很高兴,拽住牛淑芬和钟玉花就不撒手,说话也好听,道:“这俩姑娘真俊儿,仙女儿似的。你们爹妈了不起,怎么生出这么好看的姑娘呢。”
牛淑芬和钟玉花红着脸,不好意思往出拽手。
表姐佟玉华大声对外婆说:“奶奶还不松手,你把人家的手都拽疼了。”
外婆这才不情愿地松开手。
外婆身板硬朗,声音清脆,布满皱纹的脸既威严又不乏慈祥。在她一大堆孙男外女中,外婆对我最好,有时,当着二舅妈的面,就直接夸我:“你看人家守义,多聪明,哪像你们养的那堆东西,一个个笨驴子似的。”二舅妈不高兴,反驳道:“你也不看看你家啥根儿,猪能生出麒麟来?”
外婆听说我要带同学去河套,叨唠开了,嘱咐我们,不要钻柳条通,里面有狼,不要下河,能淹死人……过去,外婆很少说废话,看来,外婆也老了。
从外婆家回来后,大姐、二姐还没睡,将屋里屋外都收拾干净了,炕上铺满了被褥,女的在里屋睡,男的在外屋睡。
我第一次做成一件事儿——请同学来家玩儿,心里很兴奋,再加上做饭做菜多,大炕烧得热,一时间睡不着,就一个人来到外面的大杨树下。
这棵大杨树,是棵野杨树,不知生长了多少年。我父亲选择在这里建房,就是看中了这棵大杨树长得茂盛,说这里风水好,房子建好后,大杨树便成我家的了。但父亲也不单独霸占,在树下打了一张桌子两个长条凳子,让大家没事儿来此乘凉唠嗑儿。
我在树下刚坐下不久,牛淑芬也出来了。
牛淑芬说睡不着。
牛淑芬挨着我坐在凳子上,瞬间,那股大丽花一样的气息马上传给了我,让人感到很惬意,很温暖。
我们坐在一起,看着美丽的夜色。
夜空一片钢蓝,撒满白花花的星星,亮亮的天河就弯在头顶。夜空下,是我们的屯子,黑乎乎的,静得没有声息。从我们坐的这里往东看,是黑黪黪的东大甸子。甸子上,燃着几处火堆,那是放马的人点的。马随祖先,为了安全夜晚出来吃草,就是到了现在这些马儿也没改变这个习惯,让人贪黑放牧,正所谓马无夜草不肥。东大甸子除了野火,还有萤火虫,黑暗中,这里亮一下,那里闪一下,飘来飘去,将大甸子勾勒得一片神秘。
平时在班级,我和牛淑芬说话无拘无束,现在单独坐在一起,尤其在这静谧的村庄和荒野渲染下,却不知说什么了。我能听到牛淑芬清晰的鼻息声,甚至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后来,还是牛淑芬打破了沉静,说道:“你大姐长得真漂亮,像电影演员似的。我敢说,咱们靠屯街,再也找不出像你大姐这样漂亮的姑娘了。”
牛淑芬对大姐的赞美,说的不是假话。大姐长得确实像电影名星,但是,一个乡下姑娘,再漂亮有什么用?想到年纪小小的大姐马上就要结婚了,还是嫁给她不喜欢的男人,我不由叹息一声。
牛淑芬听到了我的叹息,问道:“怎么了,守义?”
我告诉她,大姐明年就结婚了。
“结婚,为什么要结婚?她多漂亮啊,怎么还结婚?”
牛淑芬单纯的问号,让我感到好笑,但我没笑,告诉她,我大姐订的是娃娃亲,是我父亲订下的,无法更改。
听了我的讲述,牛淑芬明白了,说道:“没想到你父亲这么传统。这事儿就是一个玩笑,能算数么。我父母的同事,有时领个儿子到我家,说让我给当儿媳妇,我父母也答应了,可这能算数吗?我要是你大姐,打死也不干。”
“你要是我大姐就好了,我哪有这样的福啊。”
“我比你大,就是你姐。”
牛淑芬和我同年,我们也没论过生日,不知道她怎么会说比我大?牛淑芬说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一把抓住我的手。我感觉全身一震,正不知如何时,牛淑芬似乎也感到了自己的冲动,想要抽回手,却被我攥住了。牛淑芬的小手光滑柔软,握在手中凉凉的肉肉的。一摸就知道,这样的手,是从不干活的。牛淑芬没有往回拉手,任由我握着。黑暗中,我们谁都不说话,看着满天星斗,看着萤火虫明灭的荒野,心里涌过一种近乎忧伤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握一个女孩子的手,而且,还是一个让我心怡的女孩子的手,那一刻,我的心纯净得如同天上的星星,没有一丝杂念。这并非我当时还小,在农村,从大人小孩的骂人话中,从猪牛狗羊的交配中,我早已完成了一个孩子的性启萌,但是,正如一个人面对着一朵美丽的鲜花,欣赏还来不及,哪会想到别的。那一刻,我不知道我们手握了几分钟?也许是一分钟,也许是两分钟,也许是半个小时……总之,这第一次握手,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后来,大姐出来起夜,我俩像被烫了一下撒开手,装成没事人一样,回屋睡觉了。
那一晚,我失眠了,满脑子都是牛淑芬的手。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吃完早饭,动身前往大河套。
大姐要看家和照顾四妹玉兰,她让二姐随我们前往,这让二姐很高兴,忧凄的脸上,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守礼不用说,带不带他,他自己有腿。另外,还有表姐佟玉华表哥佟万贵,我们一行九人,浩浩荡荡,奔向我家的大河套。
老天爷像被我们的情绪感染了,将天亮得一片高远、湛蓝,让人的心敞亮得透明。
刚进入大河套,还山重水复的,草木长得粗野、荒凉,不久,柳暗花明,所有的美“呼啦”一下全推到了眼前:清澈的大河、扳罾网、渔船、房子、庄稼、瓜果、青菜、果树……懒洋洋的猪,乱刨的鸡,而在这一切中,更有河边地头那一畦畦花卉,步步高、扫帚梅、鸡寇花、大丽花……此时都竟相开放,将大河套点缀得如同仙境一般。
同学们吵吵巴伙,以为来到了世外桃源,几个女生更是大呼小叫,这让我的心,多少有了一丝儿满足。
妈妈看我一下子带来这么多同学,很为自己的儿子自豪,能摘下来的瓜果,都被她摘下来了,在门前摆了一大桌子,简直就是一个水果摊儿。父亲也很高兴,难得说出一句温情的话:“孩子们,你们吃吧。只要伊通河不发水,我保证大家啥时来都有好吃的。”
听了父亲的话,同学们都乐了,自然不客气,抢着喜欢的水果吃。
水果还没吃完,谭斌和张中原就瞄上了父亲的扳罾网,守礼便带着他俩去扳鱼;牛淑芬、钟玉花、佟玉华,看上了父亲新造的木船,我责无旁贷,便和佟万贵带她们去划船儿。
这一天,父亲确实发了龙恩,平时我要玩船,他眼睛一瞪,我赶紧下来,这回,听说我们要划船,不仅没阻止,还嘱咐我们注意安全。
回龙崴子波平如镜,水流缓慢,映衬着两岸的灌木丛,柳丝轻抚水面,野花点缀河边,很多蜻蜓,贴着水皮儿飞着,往水里产卵,这让小鱼和青蛙得了机会,经常跳出来,将蜻蜓当成美餐。受到我们惊扰,不时有几只捕鱼的水鸭子被惊起,拍打出一片水花飞向远处,而就近岸边的土崖上,也经常有晒太阳的老王八,“啪啦”一声跳入水中。
美丽的回龙崴子,荡漾得心旷神怡。
牛淑芬坐在船中间,看着划船的我问:“守义,这里为何叫回龙崴子?”
没等我回答,钟玉花抢着说:“那还不简单,一定是乾隆私访,走到这里就回去了。他是龙,所以这里就叫回龙崴子。”
牛淑芬说:“别瞎掰了,乾隆私访是下江南,怎么会走到这里?让守义讲。”
我笑着说:“钟玉花说得也沾边儿。大清时,打老毛子的雅克萨之战,就是从这条河上运粮。传说,当时康熙皇帝就坐在运粮船上,来到这里时,被几位大臣力劝,才回了朝庭。另外,这里还有一个传说,说一只松花江的大乌龟,沿河寻游时相中了这里,用了三天三夜,将这里泬出个大崴子,来当它的行宫。”
听完我的故事,牛淑芬瞪我一眼,说道:“你比钟玉花还能瞎掰,哪有那么大的乌龟?就算有,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本事。”
我没有回答她,以桨当舵,任由船儿在水面慢慢飘荡着。
牛淑芬和钟玉花,都沉醉在这如梦如幻的景色中。她们忘记了说话,睁着大大的眼睛,一会仰望着蓝天,一会用手轻拂着水面。
我一边把握着船的方向,一边欣赏着我这两个女同学。
牛淑芬比钟玉花高半个头儿,水汪汪的杏核眼,衬托着白净的瓜子脸,再加上棱角分明的鼻子和嘴,使她显得清秀而窈窕;钟玉花却如同一件小巧玲珑的工艺品,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被安排得恰到好处,尤其一张椭圆形的小脸,娇嫩得让人不忍触摸,当然,也不敢触摸。她俩都扎着羊角小辫,系着粉红色蝴蝶结,翻领紧身白衬衣,天蓝色短裙。白衬衣下,隐隐突出乳房的影子,虽不算饱满,却足以显露少女的风采了。
就在我尽情欣赏她俩时,牛淑芬看着我说:“守义,你太自私了,这么好的地方,以前为什么不领我们来?”
钟玉花也装成生气的样子说:“就是,你早该领我们来了。”
没等我回答,表姐佟玉华插话:“你俩偷着乐吧,别说你们,就我这个表姐,也是第一回坐他的船。”
看牛淑芬钟玉花故作生气的样子,感觉很好玩儿,我逗她俩,一边划船,一边抬高桨,往她俩身上撩水。
这下惹了大祸。
她们发现我是故意的时,边笑边往我这边跑,要抢夺我手里的桨。她们不掌握平衡,都扶着船的一边往船尾靠拢,霎时间,船身倾斜,小船左右摇晃,越晃越厉害,她们站也站不稳,蹲也蹲不下,惊慌失措地不知在喊些什么。
我一时也惊呆了。
如果翻了船,我和佟万贵水性再好,在这么深的水中,要救起她们三个姑娘,也是困难的。
我大声喊着:“快蹲下,两手分开,一手把一面船帮。”
“不要乱动,坐稳了,不然翻船了。”佟万贵也着急地喊起来。
她们很听话,马上静下来,两只小手分开把住两面船帮,既不敢站也不敢坐。
总算有惊无险,船慢慢平稳下来。
望着她们吓得煞白的小脸,我后悔方才开的玩笑,说道:“现在可以坐下了。”她们坐下后,钟玉花眼睛始终盯着水里,一会儿抬起头小声说:“不会是那只大乌龟捣鬼吧?”钟玉花的情绪感染了牛淑芬,连表姐佟玉华也被感染了,她俩也将目光投向水里,好像那只大乌龟,真的就在水里,就在我们船下似的。
我笑着说:“不要看了,哪有那么大的乌龟呀,逗你们玩的。”
她们没说什么,但我看出她们还是很担心,我也没了继续划船的兴致,我说上岸吧,她们也没反对。
我把船划到扳罾网下,船还没靠稳,谭斌和张中原站在扳罾网旁,喜形于色地喊道:“看我们扳了多少鱼,还有一只大乌龟!”
我扶好船,让她们一个个安全上到岸上。牛淑芬弯腰看沉在水中的鱼囤子,一看,惊呼起来:“这么多鱼,还有那么大的,唉呀妈呀,真有一只大乌龟!”
我一看,他们确实搬上来一只大王八。
伊通河里没有乌龟,但有乌龟的本家兄弟——王八。王八学名中华鳖,有的地方叫甲鱼,有的地方叫水鱼,有的地方叫团鱼……回龙崴子里有很多王八,但是,父亲受萨满文化影响,从不伤害它们,每次扳到都放生了。父亲听我们吵吵巴伙说扳到了大乌龟,过来一看,对大家说:“放了吧。”
牛淑芬说:“大爷,咋能放了呢?它的肉很好吃,我吃过。”
父亲道:“咱这里是崴子边儿,还托它保佑不发大水呢,另外,它也能帮着往网里赶鱼。”
在大家一片“哦”声中,父亲用网兜将王八捞出来,那是一只三斤多重的大王八,脊背黑黄,小脑袋紧缩在腔子里,显得十分紧张。父亲将它放进河中,它一转身就不见了。
父亲可能看出大家失望的眼神,说道:“咱这里鱼多得是,就不要吃它了。”
牛淑芬善解人意,说道:“对,咱们不吃它,让它帮咱们赶一条大鱼来。”
牛淑芬说完,就去拉扳罾网的绳,可是,她的小脸憋得通红,却没拉动。守礼、钟玉花、谭斌都上去帮她,随着梯形网绳被拉下,网从河里渐渐浮起,说也奇了,当网底露到水面时,一条三四斤重的鲤鱼和两条半斤多重的鲫鱼在网底噼啪乱蹦。牛淑芬乐得大声高喊:“乌龟显灵了,帮我们赶来鱼了。”
父亲见此,也十分高兴,说道:“你们别扳鱼了,这活儿累。守礼,你带你们去地里吃瓜。”
我知道父亲的心思,他说的活儿累,是嫌我们这些孩子在网前吵闹,影响鱼儿进网。
听父亲如此说,大家都跑到地里,夸张地选着自己爱吃的瓜果,直到肚子装不下为止。
守礼小尾巴似的,一直跟在我们身后。守礼人小,耳朵好使,一会儿告诉大家,说听到野鸭崽的叫声了。
钟玉花抬起头,细听一会儿,说:“真有。走,我们去抓野鸭崽。”
我们循着声音,向地边灌木丛中钻去。
灌木丛里又闷又热,随着我们经过,一群群蚊子被惊起,见肉就叮,就在我要放弃时,守礼指着远处说:“大鸭子在那呢。”果然,一片柳蒿下蹲着一只枯草色的大母鸭,不细看,很难分辨出它和枯草来。守礼说:“有母鸭,就有小鸭。”守礼是这方面的行家。守礼说完,就向母鸭奔去,母鸭“呱”地叫了一声,并不飞走。大家都看出了其中蹊跷,向着母鸭跑去。母鸭在柳蒿丛里东钻西跑,在大家包围中,眼看就要抓住了,母鸭这才“哗啦”一声飞起来,在母鸭飞起的地方,一群黑黑的小野鸭崽儿东奔西蹿……大家各使本事,一下子抓住好几只。
钟玉花抓到了两只,牛淑芬抓到了一只,两人拿着绒绒的小野鸭崽,乐颠颠往脸上贴着。
就在这时,守礼惊恐地喊道:“二哥,狼,那有两只狼。”
一听说有狼,同学们马上把我当成依靠,全都靠向我。大家顺着守礼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前方三十多米远的一处土岗上,站着两只草黄色的大狼。狼早已看到了我们,尾巴拖到地面,竖着尖尖的耳朵,垂着长长的舌头,阴郁的眼睛冷冷地看着我们。
面对着狼,同学们谁都不敢说话了,一个个小脸吓得煞白,牛淑芬不知何时,抓住了我的手。牛淑芬一抓到我的手,我的情绪稳定下来了,说道:“不要怕,我家有洋炮,咱们一喊,我爹就来了。”
我刚说完,守礼就喊起来:“爹呀——妈呀——有狼——”
大家七嘴八舌地喊起来:狼来啦——
沉闷的大河套,被我们的喊声震醒了。
听到我们高喊,狼不所所措,就在这时,一声劈雷似的老洋炮声响了起来。空阔的大河套,遍地都回荡着老洋炮的轰鸣声。
狼听到洋炮声,全身一震,马上灰溜溜地离开了荒土岗,钻进灌木丛去了。
父亲提着老洋炮,母亲提着砍柴刀,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就在这时,钟玉花大叫一声“妈呀”,大家一看,她伸开手,手上的两只小野鸭崽全捏死了。大家刚看完死鸭崽,谭斌一扭头,看牛淑芬依然抓着我的手,问道:“你这是干啥呢?”牛淑芬听赶紧撒手,脸“腾”地红了。
大家一阵开怀大笑。
父亲将我们带回房子,母亲已将鱼炖好了。人多,母亲炖了满满一大锅鱼,鱼上边,还贴了一圈金黄的大饼子。
水清鱼活,再加上母亲手艺好,这顿午饭,让我的同学们一个个吃得满头大汗,谭斌吃得鼻涕都流出来了。
这顿饭,也是我这辈子招待同学最好的一顿饭。